韩愈的原道与洛克的理性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往往是批评当下社会风气不好的常用语。这句话里有个前提,以前的风气比现在好,古代的风气比今天好,要消除当前世道的弊端,只能从古代讨要秘方,只能从古代寻找根据。这样的话重复来重复去,就会形成思维定势,甚至形成复古派系。
从古代社会讨要拯救新弊端的秘方,从古代寻找改造新弊端的根据,在中外都有。前者如唐代的韩愈,后者如英国的洛克。

(韩愈)
韩愈的《原道》可以作为分析的标本之一。在我国,虽然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文并不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出的,《汉书·武帝纪》只有“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董仲舒传》的表述是这样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将此概括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八字方针,其实出自五四时期的易白沙,见《十家论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29)的指导方针,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得到贯彻。且不说汉朝建立之初,崇奉的是黄老之学,汉武帝确立崇儒方针,等于否定了其先辈曾经创造了“文景之治”的行之有效的治国方针。即使他确立了崇儒方针,也并未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而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强盛王朝——唐朝,历代帝王特别是前期的几位皇帝崇奉的并非儒教,而是道教,他们不仅将道教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甚至在李唐之李与李聃之李之间建立起血缘联系。即使在晚唐,一些皇帝对于佛教的兴趣也远在儒学之上,这也是韩愈撰写《原道》(《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83年,页579)的动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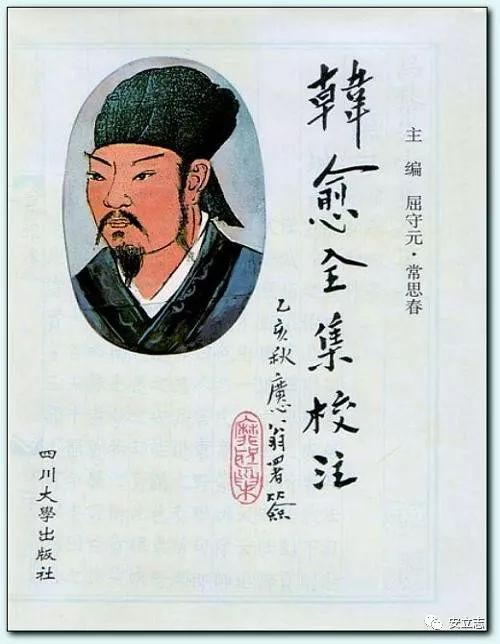
《原道》的宗旨在于反佛道以尊儒教,正是从这点出发,他才将儒学称为“原道”。在他看来,在“人之初”的年代,也就是在人类还在穴居树栖,渔猎采集,茹毛饮血的阶段,儒家的圣人就应运而生了(“有圣人者立”),他们“为之君,为之师”(同上书,页581),教这些初民“以相生相养之道”,他们如同东方的救星、印度的观音、西方的耶稣,创造了人类,驯化了人类,他们为初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同上);他们“为之衣”“为之食”,解决了初民的温饱问题;他们“为之宫室”,为初民解决了“木处而颠,土处而病”的困境;他们“为之工”、“为之贾”,创造了工商业;他们“为之医药”、“为之葬埋祭祀”,解决了初民的就医丧葬问题;他们“为之礼”、“为之乐”、“为之政”、“为之刑”、“为之符、玺、斗斛、权衡”,解决了初民的心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伟大的圣人是什么呢?“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同上书,页582)由此可见,圣人就是帝王。韩愈斩钉截铁地宣布:“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同上)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也就是说,没有帝王,就没有人民!
圣人是无所不能的,他不仅创造了“士农工商”这些基本的社会阶级,而且建立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君、臣、民的差序格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同上书,页582)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角色或曰社会地位。如果说君、臣、民三者的角色有点儿像掌权者、执行者、劳动者,倒不如说更像牧羊人、牧羊犬与羊群(这种关系可简称为“人——犬——羊”),在他的语境里,人民如同羊群,他们只有向牧羊人提供羊毛、羊肉、羊奶的义务,如果提供的不及时,不合格,就有可能遭到牧羊犬的欺凌与伤害。韩愈进行这样的论述,其内心深处似乎隐含着一个逻辑:“一切人都生来处于政府之下,因此他们不能随意开始创立一个新的政府。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他的父亲或君主的臣民,所以他处在臣服和忠顺的永久束缚之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页71》)韩愈说的很明白:“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古文观止今译》,页582)这些话,说的通俗一点,无非还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君要像君的样,臣要像臣的样,民要像民的样。君、臣这些“劳心者”虽然是民这些“劳力者”养活的,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基本规则是不能改变的。只不过,韩愈对待“民”的态度太过恶劣,“事其上”的义务即上缴赋税的义务履行的不好——“则诛”,这态度,这立场,恶狠狠、血淋淋!同是儒家传人,同样论述君民关系,孟子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258)然而,这个韩愈却是以孟子传人自居的,他“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1935年,页268) ,然而,在他与孟子的比较中,他所坚持与阐述的似乎并非儒家的原道。苏东坡谓韩愈“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509),的确言过其实。
如同韩愈一样,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或者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体系,洛克也从遥远的古代说起。洛克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比韩愈晚了将近8个世纪。他们二人在时代、文化、地域背景上有着极大不同,但是,在原始人类的角色与地位这一点上仍是可以比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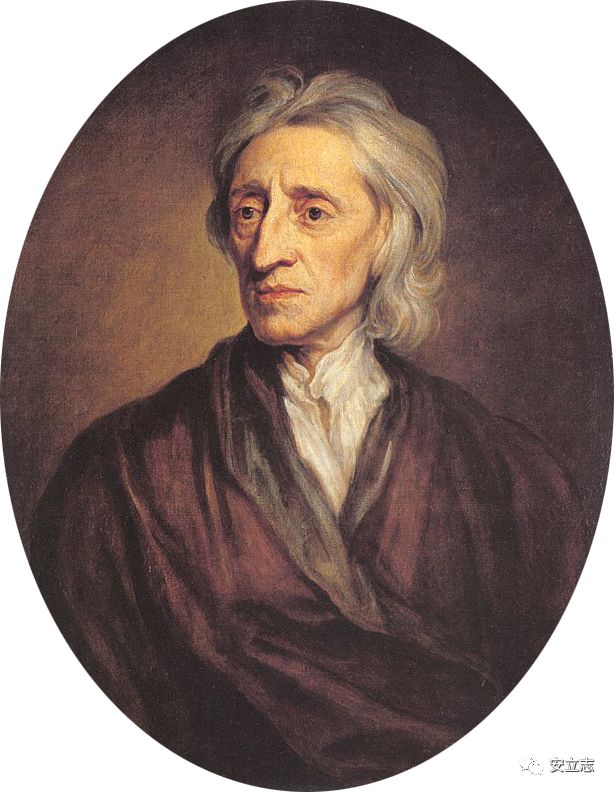
(约翰·洛克)
洛克没有“原道”这样的说法,他所描述的是人的自然状态。虽然他曾讲过人是创世主(上帝)的创造物,但在他之后的阐述中,这个创世主似乎总不在位。他指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政府论(下)》,页3)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平等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同上)在这里,并没有从天而降的圣人来拯救和教化他们。如果说韩愈的“原道”描述的人类最初状态是一种“人——犬——羊”关系,那么,在洛克的笔下,自然状态的人们就像一群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啃食青草的羊群。
原始人类的内部机制是怎样的呢?洛克强调,“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服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同上书,页4 )洛克所说的“理性”,也被他称为自然法,大概相当于初民遵循的规则,在地位上与韩愈“原道”的字面意思有些近似。这样的“理性”,很自然地排斥了居高临下对人们进行教诲与驯化的任何圣人与君主,他们内部完全处于一种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状态。

由于环境的制约、外敌的入侵、内部的竞争等因素,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逐渐有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然而,洛克认为,“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而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同上书,页59)这种组织起来的方式,既不是战俘营,也不是劳改队,甚至不同于强制性的牵牛入社,作为后来者的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与洛克的设想似乎异曲同工。这些原始人类“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同上书,页61)从300多年前洛克绘制的政治蓝图中,已经可以隐约看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制度与国家政体的运作机制。在某些阶段上,人类自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确曾存在过,比如北美早期移民,对于他们来说,“有国才有家”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那里,大都是先有居民点,再有社会组织,后有政府机构,最后才建立国家的。
韩愈和洛克作为思想家,他们根据自己的理念,设计心目中的理想国。韩愈与洛克的理念之所以反差如此巨大,并不仅仅在于两人之间的时代之差,起根本作用的正是深入骨髓的文化与社会传统。正是古代华夏的专制文化,让韩愈想当然地将君、臣、民(亦即人——犬——羊)格局,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社会模式,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的文化窠臼。而在洛克看来,任何专制权力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人类文明应当拒绝与摒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主的臣民或不如说是奴隶来说,……当他的财产受到他的君主的意志和命令的侵犯时,……好像他已经从理性动物的共同状态中贬降下去似的,被剥夺了裁判或保卫他的权利的自由;从而有遭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危险,而这些灾难和不幸是很可能由一个既处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状态而又因受人谄谀逢迎以致品德堕落并且掌握着权力的人造成的。”(同上书,页55-56)
有人或谓,无论前者的原道,还是后者的理性,并非人类经历过的真实历史,因而他们的推测和设想,不过是空中楼阁。的确,人类的远古状态,往往无法验证。即使在华夏古国,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多到殷商时期,至于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以及儒教门徒言必称的尧舜禹,大多只是传说而已。有文字可考的中华文明,安阳殷墟提供的证明,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云云,大概是将那些石斧、石刀统统作为证据了吧!
价值的差异,理念的不同,在韩愈和洛克之间,大概与文明的阻隔有关系。几百年前,当地理大发现与世界市场形成之际,分处于地球不同方位的人类,逐渐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比如海洋贸易、自由市场、代议制政府等等。当今之世,已是地球村,相信韩愈的“人——犬——羊”的社会政治格局,已被多数国家所抛弃,民主共和政体(尽管在具体形式上也有差别)已经成为全球多数国家的选择。当今时代,回头再看韩愈的“原道”与洛克的“理性”,抚今追昔,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