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说这段话,发自肺腑还是假惺惺
文/俊祥 运营/祥哥
两宫西狩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旅程。王文韶在家书中谈及,“两宫自京启跸情形,所谓天子蒙尘,从古稀有之惨,可痛已极”,并具体描写道,“太后身穿粗蓝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带,灰色战裙两条,铺盖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褥,无替换衣服,亦无饭吃,吃小米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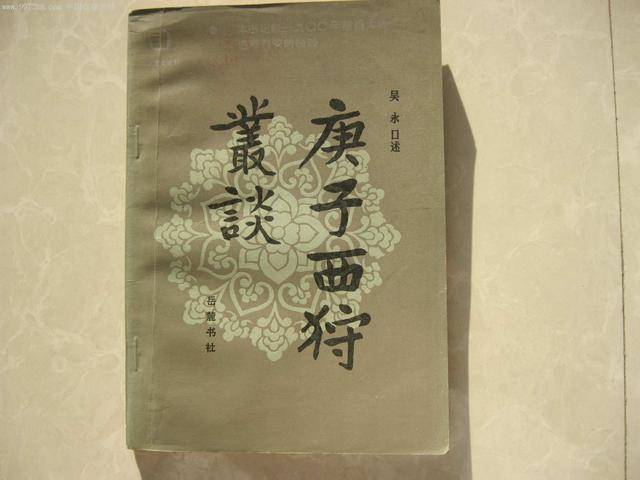
慈禧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这样的悲惨境遇,促使了慈禧的反省。
据吴永记载,慈禧曾对他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
事后的追忆中,慈禧也曾悔恨地说:“综余生平,惟此谬误。”

慈禧对其利用“拳匪”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其中对义和团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固然仇恨不已,但也蕴含着对自己决策失败的懊丧。
同时,这一段西逃历程,让慈禧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情景,促动了慈禧内心的愧疚之情。据《慈禧外记》载“太后由京往西安,及由西安回銮,见沿路农民贫苦之状,甚为悯念,特发银以赈之,其数甚巨,并告皇帝曰:‘前在宫中,不知小民之苦也。’”
吴永亦曾追述说“余之陪銮也,往往不次召对,每陈民间疾苦,及闾阎凋敝情状,慈圣辄为嗟叹”。虽然“甚为悯念”,只是“见沿路农民贫苦之状”后产生的,虽然“嗟叹”只能在有人“陈民间疾苦”时才会发生;然而,这却使慈禧深切体会到自己统治下民众的苦难生活,进而产生了“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的感慨。

在这种愧痛的心理作用下,在一定时期内,慈禧是比较关注民生的。1900 年山西大旱,“秋成大半无收,灾区甚广”,以致于“粮价昂贵异常,小民流离转徙,困苦情形,殊堪悯恻”。政府开办粥厂,也难以济事,故而慈禧下懿旨,发银 40 万两,交给岑春煊,“妥为赈济”。后来她又命令刘坤一将江苏的留存海运漕粮运往陕西。
另外,在“西狩”途中,慈禧也感到有愧于光绪帝。《崇陵传信录》谓:“上视在京日稍发舒矣”。《慈禧外记》也描述说“在西安时,皇帝时或参预国事,较在京时稍为自由。此戊戌后之所无者”。
《书庚子国变记后》一文中回忆了慈禧西狩时扈从帝后的某官员的话:“西后自出险,恒语伺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日,召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帝曰:‘论国法,彼罪不赦,乌论敌如何?’漪等颡亟稽。时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尔谓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犹闻咨嗟声。漪等出,步犹栗栗也。未几,刚毅恚而死。”

史家李剑农分析说“西太后当时就是对于光绪帝,也现出一种羞愧不能掩盖的样子”。正是因为“愧痛”,光绪才能痛斥载漪和刚毅。在闯下大祸,光绪帝发威慈禧又不便回护时,载漪等人才会“步犹栗栗”。此时的慈禧认识到了自己和曾经信任的王公大臣的错谬。胡思敬曾言道“庚子西巡以后,孝钦深自引咎,内惭其子”,正因为对光绪的愧疚,才使得光绪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产生相当的威慑力。
慈禧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当她亲身体会到民生凋敝的惨况,面临国将不国的困境时,她会愿意施行一些善政,试图改善一下民众的生活和王朝的处境。“后自蒙变,毅然思与民更始”,这是符合人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往往忽视被研究者的“人性”,这一忽视使我们的研究结论脸谱化,变得单调乏味。就拿慈禧来说就不能剥夺她内疚惭愧的权力,既然作为最高统治者,她能尝到“有平民所不堪者”的艰苦,那么“愧痛”就应该是她心理的真实流露。

慈禧在“西狩”途中,从《辛丑条约》的内容中,都认识到庚子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后果,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补救,“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庚子之变使慈禧内心中产生的较为强烈的变法需求就成了新政的诱导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