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子弹带来的“记者节”
来源:《新闻周刊》
一年一度的记者节从2000年11月8日确立,至今已有22年了。追根溯源,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中国的记者节。从1934年到1949年,每年的9月1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都会举行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民国时期的记者节,缘自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当时江苏省会镇江轰动全国的“刘煜生案”。1933年1月21日,镇江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
该案是我国新闻史的重要事件,是国民政府建立后发生的第一起报案,也是唯一一起新闻工作者以文字狱被错杀的冤案,在新闻界掀起抗议的滔天狂潮,并直接促成了后来的民国“九一”记者节。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刘煜生与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相提并论,认为他敢于仗义执言,才招致杀身之祸,赞誉他“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

刘煜生原籍江西南城,幼年时因家庭变故,随母亲来镇江投奔舅父,此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刘煜生早年学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自任主笔,并兼任报馆经理。“江声”即“镇江之声”的简称,寓意报纸为镇江民众的代言人。《江声日报》的主要内容有国内外要闻、本地新闻及广告等;副刊有《文艺》、《野芒》、《呼声》等。在刘煜生的苦心经营下,该报逐渐形成了消息灵通、报道翔实的特色。刘煜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的报刊总能直击社会病症。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的办报风格,《江声日报》深受民众的欢迎。
1929年春,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至镇江,镇江成了江苏省省会。刘煜生继续坚持《江声日报》的办报风格。《江声日报》的地位愈加重要,影响力迅速得以扩大,成为当时江苏省内颇具社会影响的报纸。
1931年,永济洲佃农因灾荒无法向焦山寺庙交租,镇江县政府为强迫农民交租,关押了几个农民。刘煜生以记者身份指责镇江县政府关押农民多日,有违法律,并请全国律师代表张迈出面弹劾县长,迫使县政府释放被关押农民。刘煜生仗义执言,得罪了当局,被当地权贵视为“危险分子”、“镇江一害”。
1931年底,国民政府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接替辞职的叶楚伧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一上任,即令各地设立毒品稽查所,实则从中征收税金,变相买卖鸦片。顾祝同主政江苏后,任命自己多年的亲信、儿女亲家赵启騄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赵启騄有两大嗜好:抽大烟和炒股。尽管国民政府早已颁布禁烟公约,赵启騄依然经常与“烟友”包租饭店客房大过鸦片瘾。赵启騄还酷爱炒股,每个交易日都要向上海股票交易所发出交易指令。他最喜欢横卧烟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通过电话炒股,每月长途电话费高达数千元,比蒋委员长的薪水还要高,全部从民政厅的账上开支。
一天,正当赵启騄在高级旅馆如此这般逍遥享受时,刘煜生带了照相机,冒充省府要员,瞒过茶房,闯了进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一手拿烟枪、一手拿话筒的“雅照”摄入镜头,并迅速离去。刘煜生在《江声日报》上披露了省政府官员参与买卖鸦片的内情,揭露了赵启騄的丑行,让赵在官场上十分狼狈。赵启騄对刘恨之入骨,顾祝同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两人挖空心思,要还刘煜生以颜色。
1932年,刘煜生抱着“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在《江声日报》上开辟了《铁犁》副刊。刘煜生写了一封致读者与投稿者的公开信,说明办《铁犁》副刊的宗旨是“需要斗的记述,爱的素描,是大众的呼声,是不平的呐喊”。当年1至5月,《铁犁》连续刊载了6篇抨击时弊、言辞比较激烈的文艺作品。下手的机会终于来了。顾祝同命人从这些作品中找出几段所谓的“反动”文字,如“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敲响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

顾祝同
顾祝同声称,《江声日报》刊载“左”“右”“红潮”等字眼是“宣传赤化”,又把刘煜生曾于1927年“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的旧账翻出来,说他“实系共党”。尽管刘煜生在主办《江声日报》期间,政治倾向很明显,但毕竟还不是共产党员。有一次,他对身为地下党的排字工人朱自强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很赞成你做的事。不过,我希望你更谨慎,不要使我受连累。只要我不出事,即使你出了事,我还可以出面保你。假如连累了我,连保你的人也没有了!”
顾祝同把这件事看作是刘煜生身为赤色分子的铁证。他引用了叛变的共产党员赵亚东的亲笔报告:“余于二十年四月来镇,由共党省委交下线索,得于五月在《江声报》馆认识朱自强。在余未来之前,朱已加入共党,并与省委通信,所有印刷品皆寄存朱处。朱虽为一排字工人,颇得刘煜生信任,故一切印刷品亦不避讳。”1932年7月26日,顾祝同下令查封了《江声日报》,秘密逮捕了刘煜生;又组织江苏省政府的官方报纸《苏报》发表了数篇“上纲上线”式的评论。
事实上,《江声日报》副刊《铁犁》刊载的6篇文艺作品,并非刘煜生所作。作者是一个名叫于在宽的青年学生,其叔父为当时的镇江商会主要人物。与刘一同被捕的就有于在宽和《铁犁》主编张醒愚。因为顾祝同的真实意图并非于、张二人,其家人各自一番活动后,两人很快获释。而刘煜生被长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迟迟不移送法院审理。
刘煜生被捕及《江声日报》被封,立刻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镇江新闻公会率先而起,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呼吁,要求保障新闻工作者权益。南京新闻记者公会派人赴镇江质询并要求保释,遭到拒绝。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各大报纸也发表文章声援。刘煜生的夫人张若男也在外多方奔走营救,宣称其夫因揭露官僚腐败而得罪权贵,被加罪关押,吁请有关方面对此案进行调查。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过问了此案,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行为”,希望顾祝同“准《江声日报》复刊,将刘煜生交保释放”,但顾祝同不予理睬。
在关押期间,刘煜生在戒严司令部看守所内直接上书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说明报刊文章的发表情况,反映自己的悲惨处境,请求监察院对此案进行调查。信中说,“生之生死原不足惜,特省府如斯黑暗,竟然摧残舆论,蹂躏人权而不辞,宁尚有公道可言哉……仰祈钧座迅予主持公道,既可解学生陋难于垂危,亦足挽颠倒是非于末俗,公谊私情,端赖怜悯。”
于右任看到刘煜生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之后,派出监察委员马震赶赴镇江调查。此时顾祝同恰好不在江苏,马震先后得到了省府秘书长金体乾、秘书姚鹤雏和保安处秘书冯沛三等人的接待。当马震要求查看案件原卷时,却被对方以案情重大为借口,断然予以拒绝,只得无功而返。马震在调查报告中称,“职以本案实情,未据原控人详叙,而该省府人员又含糊其辞,故令调阅原卷”,但工作人员声称“此案关系重大,案犯系奉令看押,绝对隔离,案卷亦绝对秘密,不能调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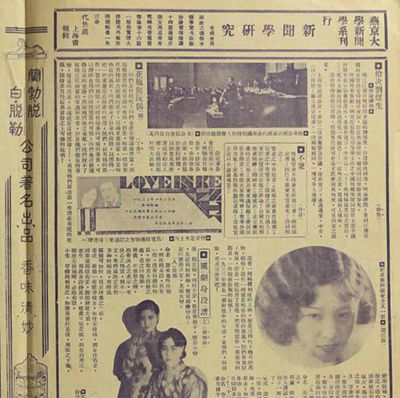
上海《申报》报道“枪决刘煜生”的新闻
于右任认为,不将此案移送法院,是违背约法;拒绝调卷,是破坏监察制度;封报捉人,是破坏法治精神。于右任要求监察院对顾祝同提出弹劾。在弹劾文中,监察院详细列举了顾祝同的五宗罪。“其罪一,违背约法,蹂躏人权;其罪二,破坏监察制度,藐视政府法令;其罪三,非法逮捕,逾越职权;其罪四,别有用心,意图陷害;其罪五,破坏法治精神。”随后,刘莪[é]青、田炯锦两位监察委员依据《国民政府弹劾法》,以顾祝同非法逮捕拘禁刘煜生、又抗拒监察院调查为由,联名对顾祝同提起弹劾,呈请国民政府应付惩戒。
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大大出乎顾祝同等人的意料。为了阻止自己被弹劾及调查程序再次启动,顾祝同决定匆匆了结此案。就在弹劾案调查开始,监察院即将正式咨请行政院饬令江苏省政府速将刘煜生由戒严司令部移送法院之际,被拘禁了半年之久的刘煜生于1933年1月21日被顾祝同命令戒严司令部执行处决,时年33岁。
死刑执行6天后,江苏省府才向行政院呈报此案,可见顾祝同“先斩后奏”的急切之心。顾祝同在向行政院的呈报中称,刘煜生早在1927年就因所谓“组织非法工会,蛊惑车夫罢工,希图扰乱治安”而被抓捕过。顾称“当时各地工会均系共党所组织,则刘煜生过去之行径,已足以证明其为共党。兹更于沪战之后,社会经济恐慌,人心不宁之时,复刊发此铁犁文字,鼓动阶级斗争”,因此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将刘煜生处以死刑。
顾祝同等想不到的是,杀害刘煜生不仅没有了结此案,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1933年1月22日,就在刘煜生被害的第二天,上海《申报》率先将这一消息见诸报端:“江苏省会戒严司令部21日晨枪决江声报经理刘煜生,其罪状为宣传共产。”短短20余字的报道,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舆论为之大哗。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于2月5日发表宣言:“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依法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
北平新闻界于2月17日举行刘煜生追悼大会,电请政府查办顾祝同。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杭州、郑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抗议电呼吁将顾祝同“予以严厉处分,以维人权而彰国法”。全国律师公会也通过决议,请求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诉讼,以维护法纪。胡适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致电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要求“将擅杀刘煜生之苏省府主席顾祝同免职查办,以重法治,而维人权”。
宋庆龄、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也以个人名义公开致电,要求政府罢免查办顾祝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刘煜生案”比作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要求为刘煜生昭雪并惩办“新军阀”。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致电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顾祝同,为刘煜生申冤。同时,江苏省内地方人士也纷纷公开历数顾祝同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以来的倒行逆施,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秉公撤办顾祝同,“以肃纲纪而安民心”。
在一片“倒顾”声中,顾祝同仍然为自己的罪行百般辩解。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他竟不顾事实称“共党刘煜生于上年拿获后,经戒严司令部审讯明确,实系共党报纸煽动文字,经证明确系该犯自撰”;“至于监察院调阅宗卷,能否对于军事机关审判罪犯之事件亦得适用,实属绝大疑问”;“其危害涉及于国家,稍不慎密,即可发生变故”。
然而,没过几日,《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在南京中山门外被暗杀,舆论再次哗然。舆情汹汹,难以平息,原来有心保顾的蒋介石,面对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深恐民怨升级,不得不做出姿态。1933年9月1日,行政院发出《保护新闻事业人员》通令,要求“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政府、军政部通令各军队或军事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接着,蒋介石被迫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免去了顾祝同的主席职务,令其退出政界,重回军界。赵启騄也于1933年10月离职经商。顾祝同卸任后,陈果夫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开始了陈氏家族在江苏省的长期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CC系”在国民党内的崛起恐怕与此案也不无关系。
尽管监察院的弹劾不了了之,顾祝同等人并未受到社会所期望的惩办,所谓《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但“刘煜生案”算是了结了。然而,由于案发前后,当局对案件的个中缘由极尽封锁之能事,造成该案不同版本的所谓的“内幕”长期流传。
顾祝同、赵启騄的党羽为替主子开脱罪责,故意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将“刘煜生案”的政治性大大降低,把它解释成一起个人恩怨,称刘煜生抓拍到赵启騄在饭店客房的“雅照”后,敲诈赵启騄。双方在中间人撮合下,达成协议:刘煜生得一笔巨款,条件是对此事严守秘密,并销毁底片。但刘煜生拿钱后并未守约,不仅未毁底片,还常常有意无意宣扬扩散此事,终于引起顾祝同、赵启騄的强烈不满,被罗织罪名,招致杀身之祸。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逻辑。因为如果顾、赵要杀人灭口,不至于把刘煜生关押半年后才杀害,可能逮捕几天内就动手了。而且,关于该案的所有正式档案中里,均未见有提及“刘赵协议”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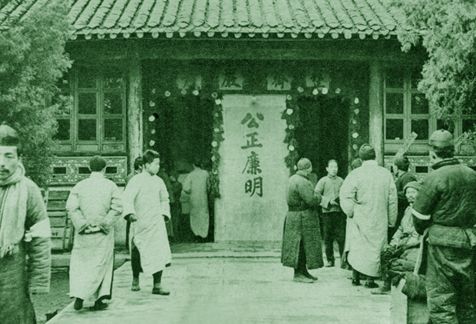
民国时坐落在镇江市中心的江苏省政府大院
还有所谓的“内幕”披露,刘煜生是个革命者,早年在上海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刘煜生平时十分关注贫民和劳工生活,时常资助他们,并在报纸上为他们说话。刘被捕的真正原因不仅是他的报社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更是因为他平时经常为地下党印刷宣传品。《江声日报》的一个员工为邀功请赏向国民党镇江市党部告发后,这些情况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掌握,顾祝同即以《江声日报》刊载“煽动阶级斗争文章”的罪名,将刘煜生逮捕羁押,半年后将其杀害。
根据这一说法,刘煜生在被捕前,已经得知军警要来抓他。他不仅没跑,还说当记者就不怕坐牢,料想顾祝同不能拿他怎样,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革命者气度。这种所谓“内幕”往往出现在建国后的某些纪念文章中,基本上可认为是对真相并不了解的人,根据顾祝同对刘煜生所加的罪名作逆向推测而得来的。
刘煜生遇害事件引发的舆论热潮,催生了“九一”记者节。首先提议将9月1日定为记者节的是杭州新闻记者公会。1934年8月23日,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发展新闻事业及保障新闻记者议案,虽经国民会议通过,并交国民政府办理在案,但亦无形搁置。追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行政院准中央执委会特令内政、军政两部,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军事机关,对于从事新闻事业人员应切实保护等。杭记者公会以政府明令切实保障记者安全,为拥护中央政令实施起见,故特决定‘九一’为记者节,以资纪念,请一致主张。”
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热烈响应。就在这年的9月1日,各地新闻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央日报》1934年9月2日报道:“杭记者热烈庆祝九一记者节,各报均刊社论。晚在中行别墅设筵,举行庆祝联欢大会。2日各报除《东南日报》《浙江新闻》二报外,都准备休刊一日。”
从1935年起,“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中央日报》1935年9月2日报道:“各地新闻界庆祝九一记者节。”报道称,杭州记者公会于9月1日举行庆祝记者节活动,并举行全国报纸展览会及阅报运动宣传周开幕式,展出全国各地报纸5000余种,其中有资格最老的《申报》第一期和香港《华字日报》,均在清朝同治初年创刊。报道还称,北平记者公会也在当日下午5时举行庆祝会,通过决议:(一)致电中央,对新闻事业及记者安全认真保护。(二)通电全国新闻界请一致主张。(三)募款赈济鄂鲁各省灾民。重庆、成都举行游艺募捐会,赈济水灾。青岛、太原、绥远、西安各报放假一天庆贺。《大公报》也于9月2日发表“记者节”短评。
“九一”记者节在民间推行10年之后,国民政府于1944年3月25日正式予以承认。《中央日报》1944年3月26日报道:“行政院核定公布,九月一日记者节,虽已奉行有年,但未经政府公布……业经社会部会同内政部呈奉行政院核定,并已转各省市政府及各地新闻记者公会知照。”
当时,不仅国统区过记者节,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也在当天举行庆祝活动。1943年9月1日,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在记者节的纪念仪式上号召新闻界“更好地反映人民辉煌业绩,更有效地粉碎反动派的一切歪曲宣传”。陆定一这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重庆《新华日报》则为纪念记者节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1946年9月1日,毛泽东为记者节题词“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朱德题词“拿着笔杆配合枪杆”。《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指出:“九一记者节,对于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个检讨总结工作、提高自身修养、改进新闻业务的日子。”

陆定一同志1943年9月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著名新闻学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劳动者统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九一”记者节才结束了历史使命。200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的请示,同意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原因是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从此,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又有了自己的节日。
有意思的是,曾经参与诬陷刘煜生“宣传赤化”的赵启騄,后来自己倒真的“赤化”了。西安事变后,顾祝同任西北行营主任,聘赵启騄任中将参谋长。在此期间,他与中共驻西安机构接触较多,对中共多有协助。抗战期间,周恩来在崂山遇险,他曾派飞机将周恩来接到西安。被蒋介石发觉后,赵启騄被革职而未再启用。西安解放前夕,赵启騄拒绝了前往台湾的劝说,留在了大陆,并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64年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八宝山公墓。《人民日报》为之发讣告,刘伯承为治丧委员会成员。
“刘煜生案”是民国时期令全国震惊的一起政治事件,在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刘煜生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履行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正如1934年1月21日人们为他举行的遇害一周年公祭仪式上所言:“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