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天皇制存续的诸因素
作者: 沈才彬 来源:《日本学刊》
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相矛盾又相统一的战后天皇制,已经生存和发展了50年。它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自然有其思想的和社会的基础。
事实上,使战后象征天皇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统治机构的连续性,思想、心理、传统权威意识的连续性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我认为尚有3种因素不可忽略:一是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树立“大众天皇制”的形象;二是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发,不断地加强和恢复天皇的地位与权威;三是国民中间仍潜藏着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
1.皇室接近国民的活动,自战败的第二年,即1946年2月便开始了。当时,刚刚宣布从“神”变成了人的天皇,为了博得国民的信赖以保持自己的皇位,并以此向盟军总司令部挑战,开始了地方巡视。过去,国民与天皇之间悬隔着一道厚重的屏障,人们只能从报刊上看到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的形象,而现在少皇竟穿着西装来到国民中间,在国民中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宣布从“神”变成人的《人间宣言》,以至于使盟军总司令部的一些官员认为,天皇的这种到处巡察是维持天皇制的战略性行动。虽然,天皇的巡察活动,最终未能完整地维护旧有的天皇制,却博得了国民的敬仰和好感。这种巡视行动1948年由于政治的原因,暂时停止。从1949年开始重又恢复。据统计,自1946年至1954年8月止的8年间,裕仁天皇共有165天到地方巡视,行程3.3万公里,足迹到达除冲绳以外的全国各地(〔日〕中村政则《战后史与象征天皇》,岩波书店1992年版)。

正田美智子
皇室与国民接近的另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11月,即宫内厅公布了明仁皇太子(现在的天皇)与“民间女”正田美智子的婚约。长期以来,皇室的婚姻,是有严格限制的。旧《皇室典范》第39条规定“皇族之婚嫁限于同族或根据敕旨特别许可的华族”,第40条规定“皇族之婚嫁依据敕许”。自明治、大正至昭和三天皇的婚姻,均依《典范》规定,没有一个越轨的。然而,明仁皇太子却摆脱《典范》桎梏,他的候选妃正田美智子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父亲是日清制粉株式会社社长,而且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对于既非皇族出身又是天主教家庭出身者能否被选为皇太子妃问题,在统治集团和皇室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在皇太子妃的选择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负责明仁皇太子教育的原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小泉信三和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他们所以选择“平民”女子为皇太子妃,是因为他们期望使闭锁的墨守成规的皇室变成开放的皇室,把天皇制置于更广泛的大众基础之上。着眼于天皇制的发展,他们在政界和皇室内进行了说服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1959年4月10日举行皇太子结婚典礼,引起了广大国民的兴趣和注意。有的学者指出,这一婚姻抉择的意义不仅在于婚姻本身,更在于它标志着战后天皇制的转折,即由绝对主义天皇制真正转化为大众天皇制。这种结果,无疑对仍然残存的天皇神权思想、国粹思想是一次打击,皇太子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冷视,但它却获得了新中间层及年轻一代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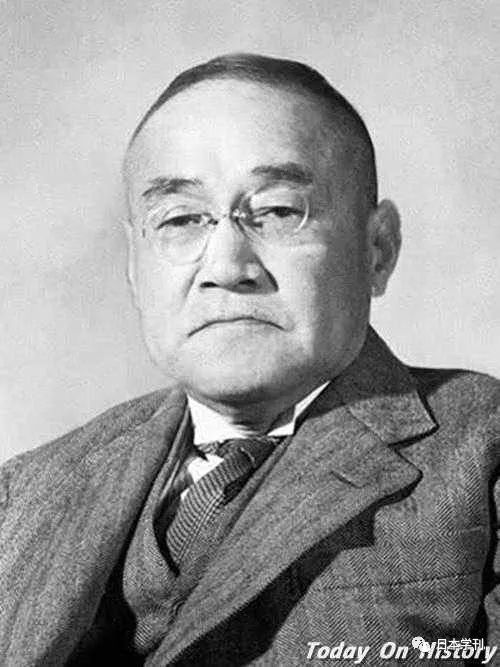
吉田茂
2.战后以来,日本上层统治集团为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恢复旧天皇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最早为维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而卖力的是吉田茂。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后,明目张胆地要复活某些旧的传统制度。吉田茂在其《十年回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出自肺腑的文字叙及他的天皇观:“在任何时代,没有父母、兄弟、长幼之序,先辈与后辈之顺,社会上下之礼仪,则社会秩序难保,国家安定难得。若据我国古来之历史观念、传统精神,皇室乃我民族之始祖、宗家。此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是传统。尊崇皇室乃是人伦之义,社会秩序之基础。我国之民主主义也应以此种观念、精神为基础。”(〔日〕吉田茂:《回想十年》第4卷,新潮社,1957年版)
吉田茂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不惜违反宪法,以首相身份经常向天皇“内奏”,并自称“臣茂”。
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放弃日本非武装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当时日本政界也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旧军部人士,如服部卓四郎等人为中心,竭力主张修改宪法第9条,加强天皇权力,建立“新国防军”,并以天皇为新国防军总帅(〔日〕秦郁彦:《日本再军备史录》,文艺春秋社1976年版)。二是以吉田茂等人为代表,主张建立从属于美军的预备队,但也不否认天皇与预备队互为不可分割的关系。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主权。盟军总司令部撤消了,但美军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驻扎日本。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界出现了以吉田茂为首的采取从属于美国路线的主流派和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首的主张摆脱美国控制、修改宪法、自主外交、自主防卫的反主流派。尽管两派政见对立,可是,在强化天皇权威,竭力推进天皇元首化问题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实现天皇元首化的基本条件是必须修改宪法。由于国民一直警惕对新宪法的修改,他们的修改宪法的企图未能得逞,天皇元首化也未能从法律上得到承认。
企图使天皇元首化的活动,在吉田内阁之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岸信介内阁时代依然十分活跃。他们以“自主宪法”为名,力主修改宪法。修改的重点自然是第1条和第9条。要将第1条的“象征”天皇变为元首,将第9条的“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实现重新武装。当时,要实现这两条宪法的修改,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上层统治者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采取了逐步变化的政策,即:首先把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精神支柱,以提高其权威;其次是使天皇拥有国君应有的恩敕权和条约批准权;第三,使天皇拥有宣战、讲和、公布非常事态宣言和紧急命令、停止国会活动等权力。(参见渡边治:《日本国宪法修改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
进入60年代以后,作为复辟旧天皇制的具体行动之一的靖国神社法问题,被推上了政界的议事日程。早在1956年3月,自民党就提出了《靖国神社法草案要纲》。由于新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作为《靖国神社法》立案自然触及宪法的禁区,因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果。60年代以后,自民党内经过将近10年的周折,终于在1969年3月拟成了靖国神社法草案,明文规定“靖国神社的目的乃是国民对战亡者及殉于国事的人们的英灵表示尊崇,举行缅怀抚慰其遗德、赞扬其事迹的仪式等,使其伟业永远流传”(〔日〕土方美雄:《靖国神社·国家神道能复活吗?》,社会评论社1985年版)。此案得到自民党总务会的通过,作为自民党提案提交国会。但由于错综复杂的政界矛盾,此提案未经国会审议便成了废案。此后直至70年代前半期,又多次提交国会,每次都未能正式审议而被废。这表明在自民党内或国会内普遍存在着对靖国神社法案的警惕与对抗。

裕仁天皇
70年代后半期,另一项复辟皇权的运动也被推上了日程,那就是年号法制化运动。自明治以来,日本的年号实行一代天皇一个年号制(即“一世一元制”)。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裕仁天皇由“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转变为“象征”天皇,但年号仍延用“昭和”。至年代后期,裕仁年已耋耄,然而新《皇室典范》等并无年号的规定,一旦裕仁死亡,必然造成年号的空白。这使政界上层和神道系统的人物颇为担忧,积极主张应使年号法制化。年号法制化的推进者们认为,这是强化天皇与国民的纽带,进一步提高天皇权威的大事(〔日〕横田耕一:《宪法与天皇制》,岩波书店1990年版)。自1977年始,在神社本厅的推动下,该运动渐趋高涨。同年5月3日,神社本厅、神道政治联盟、日本青年协议会、保卫日本会等57个团体联合召开了“要求年号法制化中央国民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福田赳夫内阁及早实现年号法制化。1978年6月14日,411名众参两院议员成立了“促进年号法制化国会议员联盟”。同年7月18日得到700个团体的赞同,成立了“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该国民会议的目标是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成立县民会议。至8月,有43个都府县议会、700个市町议会通过了年号法制化决议。在此背景下,10月3日又召开了“实现年号法制化总决起国民大会”,自民党的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出席了大会。进入80年代后,在野党的公明党、新自由俱乐部、民社党也加入此项运动。
在政界和神道界积极推进年号法制化的过程中,日本国民对此持什么态度呢?根据当时的社会舆论调查,认为“年号法制化好”的占15.1%,认为“有年号好,但不要法制化,约占64.5%。这就是说79.6%的被调查的国民同意延用年号,但大多数人不主张法制化。就在政界、神道界一些人积极推动,以及多数国民并不反对的情况下,国会于1979年6月通过了年号法案,6月11日正式公布并施行。“元号的法制化成为抬高天皇权威的一次大飞跃”(〔日〕中村政则:《战后史与象征天皇》)。
3.战后天皇制的存续和发展,皇室自身接近国民,从绝对主义天皇制向大众化天皇制转化,以及统治集团的复辟活动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还应该看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广大国民中潜藏着的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不可否认,国民的天皇观,战前战后有很大变化。1956年9月,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对大约3000人的战前战后天皇观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回答战前“尊天皇为神”和“不同于普通人”的人数占被调查人的87,3%;战后认为天皇是“普通人”和“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人数占84.8%(〔日〕加藤周一:《关于天皇制》,载《天皇制论集》,三一书房1976年版)。战前战后天皇观的大幅度转化是否表示国民对天皇和天皇制已经毫无感情并主张彻底废除天皇制呢?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年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大多数国民虽然不希望旧天皇制复辟,但也不赞成取消象征天皇和象征天皇制。东京大学的学生在战前和战后一直是比较激进的,1945年12月4日对东京大学1000余名学生的调查中,赞成废除天皇制的仅占调查总数的6%,而主张经过部分改革后继续存在的占40%,主张进行根本性改革后继续存在的占35%。可见主张继续存在的达到75%(〔日〕日高六郎:《旧意识及其原始形态》,载《天皇制论集》)。1957年7月1日号《周刊朝日》刊载了宫城音弥氏的《怎样看待天皇?))一文,其中叙及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用仪器对人们信仰天皇的程度进行了测验,其结果:主张维持象征天皇制的人占71%,主张复辟旧天皇制的占9%,主张立即废除天皇制的占9%,不关心的占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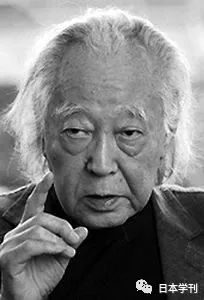
加藤周一
战后以来的各次民意调查虽然百分比有出入,但大体上总是多数日本国民赞成维持战后天皇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赞成者日渐增加,尤其是1988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探究战后50余年来日本国民对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稳定不变的态度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如下数点:第一,虽然日本国民经历了旧天皇制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灾难,旧天皇制构筑的帝国随着战争失败而瓦解,但是由于长期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国民内心的深层依然潜藏着对天皇和皇室的感情。这种潜意识的感情成为战后天皇制的精神支柱;第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广大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种新的中产阶层与战前的以农村为主体的中间阶层截然不同,它已超越了城乡、贵贱、职业和文化的局限。为了维持得之不易的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广大中产阶层希望社会稳定,而在日本能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则是天皇和天皇制。在广大中产阶层看来,维持现有象征天皇和天皇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自70年代以来,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广大国民中出现了一股追溯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热潮。通过亲身的追溯、探究,对天皇和天皇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解,在比以前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认识了天皇和天皇制与日本2000余年来历史命运的关系,从而巩固了对战后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关心和支持;第四,战后,广大国民虽然仍然对昭和天皇裕仁怀有一种潜藏的崇仰的感情,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他曾把日本国民拖入了长达15年的战争,不能不说这在国民崇仰的感情中投下了深深的暗影。然而1989年裕仁天皇的死亡,给战后象征天皇制带来了转机,新天皇明仁完全与战争无关,而且喜好学问,给人以一种亲近感,再加上轰轰烈烈的新天皇的继位典礼和皇太子德仁与外交官小和田雅子的结婚典礼,在中年、青年一代国民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后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日本青年一代对天皇、皇室大多漠不关心,然而自1989年以后,青年一代大都对天皇抱有亲近感。青年一代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好恶是预测战后天皇制发展趋势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