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质疑过战争,对大屠杀心知肚明——德国人比你想的更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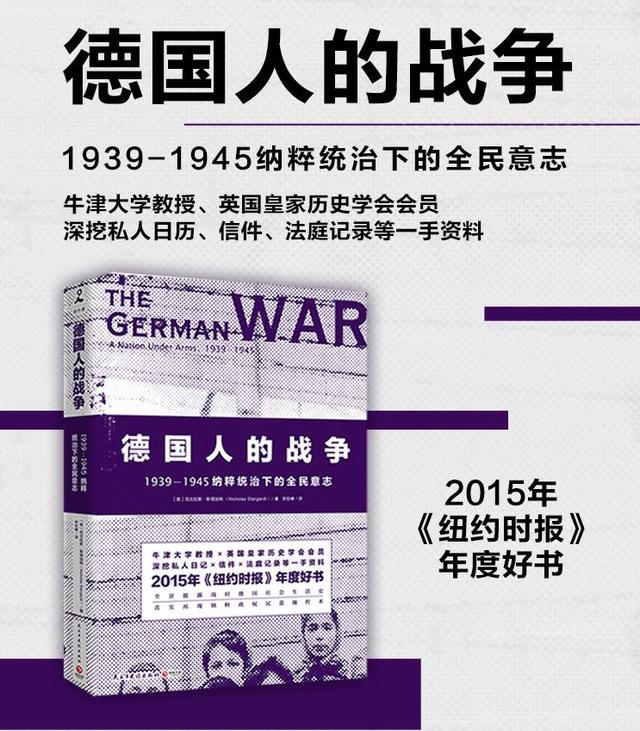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多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仍然存在非常多的争议。把所谓“人民”与“极少数战争罪犯”区分开来,是主流史学探讨战争责任的主流态度,然而事实情况远比理论和“政治正确”更复杂,而且随着微观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德国和日本是挑起战争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人们经常拿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西德前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一事被当作德意志民族真诚忏悔的例证,近年来在中国热播的德国迷你剧《我们的父辈》被赞扬为德国普通民众反思纳粹历史的佳作,这部剧表现了四名年轻人在纳粹统治期间的迷茫与挣扎,被称为德国父辈的“战争记忆”。事实上,这种“战争记忆”是极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到剪裁的。纳粹统治时代的德国人远比这些形象复杂,对于纳粹政权,对于德国发动的战争,德国人不是被动跟随、内心反抗那么简单。
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利用私人日记、政府档案和书信等详实第一手材料写作出来的《德国人的战争》一书,描绘出前所未见的德国人,这里面既有战场上的军人,也有大后方的平民。他以普通德国人为出发点,再现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失利后的沮丧和无奈、反抗,还展示出战时德国前线和后方的真实生活。
纳粹首先摧毁德国左翼社会基础,战争机器才站住脚
在传统叙述中,德国人往往也是纳粹统治的受害者,是受到裹挟,才不得不参加侵略战争和迫害犹太人等行动。《德国人的战争》却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
斯塔加特认为,德国社会具有“双重人格”,既对权力被动服从,又具有主动性,纳粹就是借助德国人主动或被动的合作,摧毁了社会民主党苦心经营上百年的社会基础。
早在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之前,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在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德国进行深耕。社会民主党通过互助会、合唱团、体育俱乐部、帛金会、幼儿园等形式,把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在政治上天然倾向左翼。
《德国人的战争》指出,纳粹党于1933年掌握政权后,就开始着手消灭政治左派,取缔了左翼政党,把至少20万人关入集中营进行“再教育”,虽然绝大多数人到1935年夏已经获释,但由左派代表的“另一个德国”在政治上不复存在。
与之对应的是,1932年底,纳粹党成员有85万人,到战争开始前夜,党员人数增加到550万人。而“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成员为230万人,“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达870万人,这些团体都利用晚间聚会和为期大约一周的夏令营等手段,举办意识形态训练课程。“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和“德国劳工阵线”作为工薪阶层和福利和贸易联盟组织的继任者,分别增加了1400万和2200万成员。到1939年,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至少都加入了纳粹党的一个群众组织。
纳粹党在打破凡尔赛和约、公开重新武装之前,对德国社会的重塑经常被人忽视,以至于有人误解纳粹武装德国和走向战争是突然发生的,斯塔加特的研究破除了这种迷思。
德国民众说不知道大屠杀,只是糊弄人的借口
在德国人的叙述中,在各种影视作品和史学研究作品中,常常把普通德国人描绘成对纳粹的战争暴行毫不知情。HBO的著名战争剧《兄弟连》中,就表现过德国军官家属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才知晓有灭绝营存在。
斯塔加特根据详实的书信等第一手资料,证明这种情况纯属子虚乌有,他指出,“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
大多数德国人通过前线亲朋好友寄送的信件和照片,以及与休假回来的和谈话,都知道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和其它暴行。集中营焚尸炉的气味四处弥漫,周围城市和乘车从附近经过的德国人都心知肚明。
柏林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笑话:“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化学家是谁?答案:耶稣,他把水变成美酒;戈林,他把黄油变成大炮;还有希姆莱,他把犹太人变成肥皂。”斯塔加特写道,15岁的孩子们“踢完足球去洗澡时嘻哈闹腾,开玩笑问在绿色的肥皂水里会有多少犹太人”。
德国国防军几乎受到神化,认为是遵守军人道德、不随意屠杀平民、不盲从纳粹领导的楷模,这种观点近年来虽然受到质疑,但《德国人的战争》对真实的德国国防军有了更为详细生动的描述。
一名国防军士兵曾经详细描述在波兰行动中参加处决犹太人的行动:
一位妇女带着三个孩子从运送犹太囚徒的巴士上下来,走向30米外的壕沟。她抱着最小的孩子,努力爬进壕沟,然后把另一个孩子抱进去,这时一个党卫队员拎起剩下的小男孩递给她。然后,这位妇女让孩子们面朝下趴在她身旁……这些人如何把枪口端到距离受害者后颈大约20厘米的地方开火。
行刑结束后,这名士兵受命铲土把尸体埋起来,他毫不犹豫的遵令而行。还有一些围观者靠壕沟太近了,以至于他们的制服都溅上了“血肉、脑浆和尘土”。很多在波兰各地目睹这些事件的士兵拍下一卷卷照片寄回家乡,然后被冲洗出来。
德军进攻莫斯科失败后,在撤退时执行“焦土政策”,比希特勒的命令还要早数个星期:
1941年12月7日,第103坦克炮团开始自图拉地区后撤时,摧毁了一切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阿尼什诺在燃烧,部队离开时,把每一间房屋都点着了,”弗里茨·法巴切写道,“我没烧掉我们住过的房子,不过其他人去烧了。指挥官也不喜欢这样,但必须这样做,目的只是想让俄罗斯人的步伐慢一点。上级不准我们询问平民会不会挨饿、受冻或者以其它方式死掉。”后撤部队焚烧了村庄和城镇,炸掉桥梁和铁路,摧毁了工厂和电力设施。在气温经常降到摄氏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天气中,士兵们抛掉最后一点道德上的犹豫,把整村的老百姓都赶出家门。
德国新教和天主教都不反对战争,与纳粹既敌对又合作
在德国,教会是最重要的独立民间机构,不少顽固的神父和牧师因为在布道坛上批评纳粹,被送入集中营。1937年7月,柏林最敢言的牧师马丁•尼莫拉被盖世太保逮捕。在第三帝国余下的岁月中,他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1945年4月,年轻的新教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佛罗森堡集中营里被处以绞刑。这两人以后都成为反抗纳粹压迫的有力象征。
然而斯塔加特指出,朋霍费尔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神学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是处于边缘化的,对当时的德国人并没有太大影响力。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朋霍费尔也一直受到埋没,后来才被宣传成德国人反抗纳粹暴政的范例。
尼莫拉不是自由民主派,而是持反犹立场的保守民族主义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潜艇舰长,虽然是神职人员,却积极支持希特勒。当战争于1939年爆发后,尼莫拉还从集中营给海军司令雷德尔上将写信,自愿再次为国尽忠。尼莫拉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对纳粹政权有异议,而非政治原因。
事实上,德国新教徒热烈支持纳粹的“民族革命”,德国天主教从宗教观点出发,对纳粹屠杀精神病人和犹太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慕尼黑大主教、枢机主教福尔哈伯和德国教会大主教、布列斯劳枢机主教伯特伦等领袖都深信希特勒是极其虔诚的信徒,使天主教会和纳粹政权在战争期间结成一种尴尬的“敌对与合作”关系。
德国人在莎翁戏剧中寻找慰藉,养鸡挖野菜应对配给
斯塔加特在书中对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也有很多生动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比英国还多。1940年,一支柏林高炮部队的人员充分利用起工作和休闲时间,值班者密切防范英国空军轰炸机来袭,不值班的人去表演《仲夏夜之梦》。1944年4月,戈培尔劝说维也纳的著名演员到柏林表示《冬天的故事》。一位德国人在日记中回忆为了去看戏,爬过成堆的废墟,“路上看到溅满鲜血、脸色墨绿的民众”。
1941年4月,电影《克鲁格总统》上映,此时轰炸伦敦和英国港口的行动正在继续,它成为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宣传医疗屠杀的电影《我控诉》在战争期间观众数累计达1530万。
德国人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配给制,开动了各种脑筋。为了获得糖,都市妇女们去乡下帮农民挖甜菜,农民用甜菜当报酬,她们拿回家熬制成糖,而且甜菜的心叶也舍不得扔,当成“菠菜”吃。
战争开始前,妇女们就把腌菜制作方法教给女儿。战争爆发后,很多矿工家庭还养起山羊或小猪。在城镇和乡村,很多家庭继续喂养兔子和鸡。就连医生这样的中产阶级也养鸡,开垦菜地。家家户户都去森林里挖蒲公英做沙拉,捡橡树果当咖啡,用甘菊、薄荷和莱檬叶当茶叶。
德国人始终相信战争是神圣的,是生存之战
德国人虽然非常不欢迎战争,生活虽然日益困难,然而并没有深刻反省为什么战争会发生。大多数德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深怀不满,确信战争是自卫性质的,是一场生存战,因为邪恶的法国人、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他们的“犹太主子”都想摧毁德国。
德国人深信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英国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其世界帝国,并削弱德国。另外,德国学童们世代受到的教育是把法国当作“宿敌”,但内心更感性的看法是把俄罗斯当头号对手。
从《德国人的战争》中可以看到,纳粹在1941年很轻松地使德国人相信,必须把新的德俄战争打到底,这样下一代人才不会再重复被俄罗斯侵略的命运。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在为纳粹政权而战,他们认为是在为家族和民族而战,这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最强根基。即使战争打到最后一刻,对东方的俄罗斯也要拼死抵抗,只愿向西方投降。
斯塔加特在书中指出,不管战争如何不受欢迎,它依然比纳粹主义更具合法性。德国在战争中期虽然开始遇到危机,却没有让德国人陷入失败主义,而是使德国人的态度更趋顽固。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质疑纳粹政权,但仍然相信战争是神圣的,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德国人抵抗到最后时刻,疯狂程度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雪洗1918年11月的“耻辱”。
在对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中,《德国人的战争》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新颖的角度,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德国和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