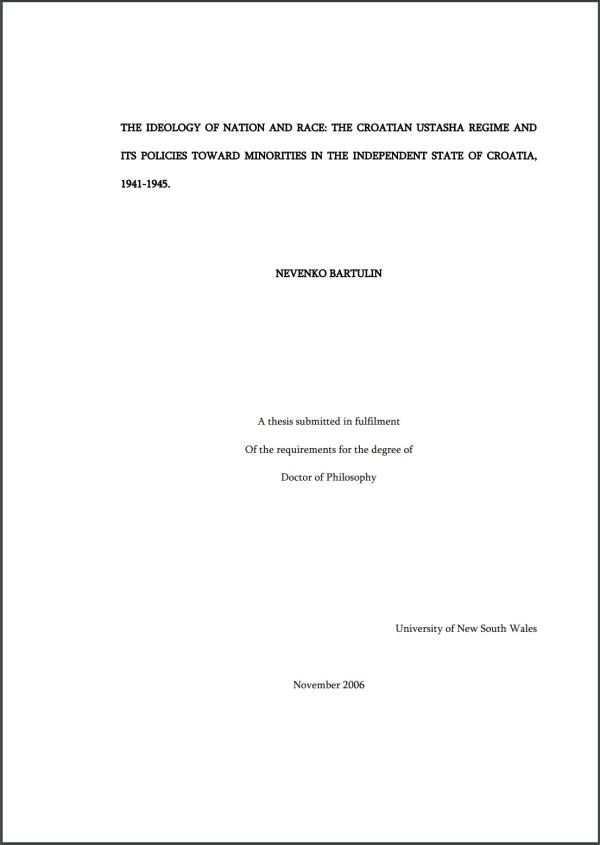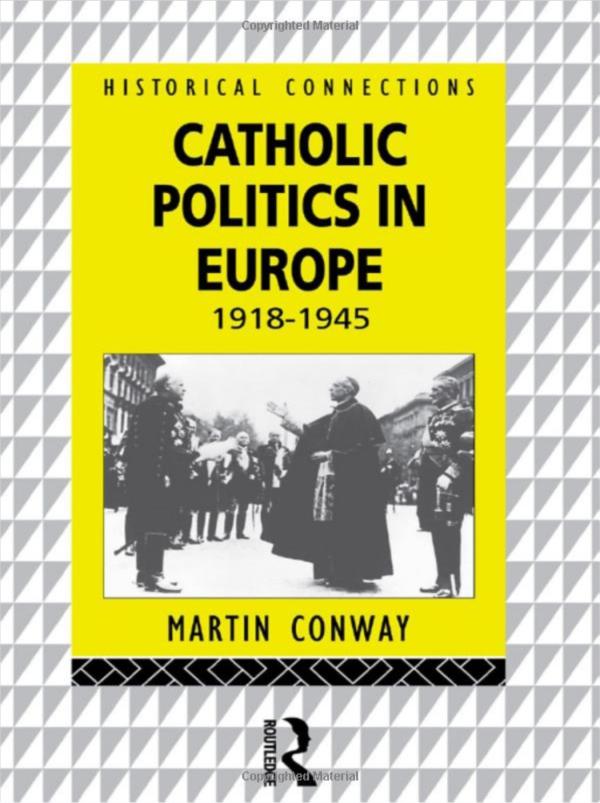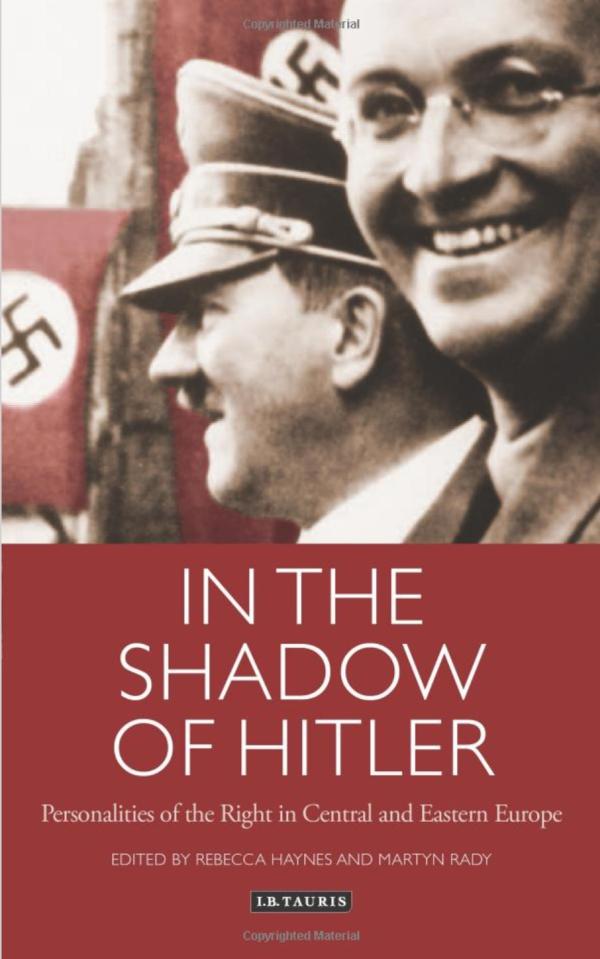在乌斯塔沙的阴影下: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运动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足球队进入了决赛。中文网络对此的反应五花八门。一些人继续每逢足球大赛就感叹想象中的“统一的南斯拉夫队”,另一些人则炮制了不少克罗地亚历史的悲情故事。不过,克罗地亚实在和“悲情”二字挂不上钩,国内也有了一些关于二战后的克罗地亚的历史科普文。不仅如此,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近年来克罗地亚足球队从球迷到队员多次因为乌斯塔沙的口号和仪式遭受处罚。这里的乌斯塔沙,就是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执政者。
从古代以来,巴尔干半岛各个民族就不断迁徙和运动。到了近代,克罗地亚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分成两股。一股以主教斯特罗斯迈尔(Strossmayer)为代表,要求南部斯拉夫人团结,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南斯拉夫运动。另一股则是以安特·斯塔采维奇(Ante Starcevic)为代表的反南斯拉夫主义。不过,后者强调的是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一套观念,和乌斯塔沙有所不同。
1918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联合之后,由于塞尔维亚方面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特别是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拉迪奇还遭到了塞族人士暗杀,克罗地亚要求分离的思潮和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乌斯塔沙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现任教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内文科·巴图林(Nevenko Bartulin)的博士论文《民族和种族意识形态: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及其对克罗地亚独立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1941-1945》(The Ideology of Nation and Race: The Croatian Ustasha Regime and its Policies Toward Minorities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1941-1945)对乌斯塔沙的历史做了详细叙述。
|
|
《民族和种族意识形态: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及其对克罗地亚独立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1941-1945》
乌斯塔沙的建立及其意识形态
1930年,克罗地亚律师安特·帕维利奇(Ante Pavelic)在意大利建立了乌斯塔沙运动。同时,他还和反南斯拉夫的原奥匈帝国克族军官们搭上了关系(156页)。有趣的是,克罗地亚独立之后,这些奥匈官员也成了克罗地亚和“欧洲”之间联系的证明,耶拉契奇(Jelacic)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萨格勒布的主要广场正是耶拉契奇总督广场。
为了达到目的,帕维利奇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使用恐怖手段。1931年,第一个乌斯塔沙训练营在意大利北部的博韦尼奥设立(159页)。这表明,乌斯塔沙运动建立伊始就刻意寻求外部力量庇护,以推动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这个外部力量,具体地说,就是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早在1927年,帕维利奇就向意大利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后者支持克罗地亚独立。作为回报,帕维利奇许诺让意大利主宰亚得里亚海,也就是割让部分克罗地亚土地(171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乌斯塔沙倒是很讲信用。
|
|
安特·帕维利奇
种族主义是乌斯塔沙起初就奉行的意识形态。在帕维利奇看来,克罗地亚人是一个独特的(因此无所谓“南斯拉夫”)、同一的种族(164页)。由此自然也就导出了如下政治诉求:清洗居住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以及居住在克罗地亚主张的波黑领土内的非克族居民。人们不难发现,这个路数和纳粹异曲同工。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伊沃·皮拉尔(Ivo Pilar)则系统地“论证”了:塞尔维亚人对社会和谐和进步有害,受到落后的拜占庭传统支配,和先进的西方与天主教对立。另一个民族主义者米兰·舒弗雷(Milan Sufflay)则“论证”了,克罗地亚民族处于欧洲和“亚洲”的边境地带,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也因此成了西方文明的卫士。舒弗雷倒不主张恐怖行动,他鼓吹用历史记忆抵抗塞尔维亚的“拜占庭-奥斯曼”传统。顺理成章地,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日益把自身定位为“欧洲-雅利安”人种(论文第七章)。很明显,这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接口之一。
和欧洲其它法西斯主义运动一样,在乌斯塔沙的叙事里,克罗地亚农民最接近自然,也因此代表了克罗地亚种族的根源(224页)。犹太人不出意外地成了乌斯塔沙的靶子,成了“克罗地亚人民”的异类,以及敌人(224-225页)。不用说,乌斯塔沙的大敌,也包括了与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30页)、“破坏传统秩序”(231页)、支持国际主义尤其一个多民族联合的南斯拉夫国家(241页)的共产党人。当时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国际共济会也被列入了这份敌人名单(239页)。当时的南斯拉夫国王卡拉乔杰维奇(Karadjordjevic)则被视为“吉普赛人”(240页),以及共济会的最高恩主(241页)。相应地,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意大利在他们看来就是古罗马精神的现实化身,以及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的先锋(232页)。
乌斯塔沙政权的诸项措施
1941年4月,纳粹德国占领了南斯拉夫,并在南斯拉夫投降前把乌斯塔沙政权扶上了台。第二个月,帕维利奇就和意大利签署三份条约,把亚得里亚海沿岸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割让给意大利,乌斯塔沙还不得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建立军事设施,以及海军(255页)。时任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曼纽埃尔(Vittorio Emmanuel)的侄子斯波莱托公爵(duke of Spoleto)也经过帕维利奇的同意出任克罗地亚国王(同上)。堤内损失堤外补,乌斯塔沙政权从波黑抢了一块地方(256页)。早在1942年,乌斯塔沙的武装就受纳粹指挥,克罗地亚士兵加入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作战。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后,纳粹接管了原先的意占区(261-262页)。换言之,从1942年底起,乌斯塔沙政权就成了事实上的纳粹保护国。对纳粹,乌斯塔沙可谓披肝沥胆、生死相随。
和欧洲不少国家的天主教会一样,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尤其是中下级教士们对乌斯塔沙政权相当欢迎,时任萨格勒布大主教斯泰皮纳茨(Stepinac)也或多或少地承认了乌斯塔沙政权的代表性,倒是乌斯塔沙方面对他颇有疑虑(339-340页)。1941年5月,时任教皇和帕维利奇进行了私人会晤(Martin Conway, 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1945, Routledge 1997,p. 83)。
|
|
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1945
乌斯塔沙掌权之后,根据制定了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底色的法律,并花样翻新,制造了一个“塞尔维亚-犹太人-共产党”的三位一体反克罗地亚阴谋神话(369页),还把南共和切特尼克来了个一锅煮(370页)。从1941年6月起,乌斯塔沙政权多次大规模驱逐并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以及波黑部分地区的居民(376-383页)。这些杀戮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各个城市和村镇。乌斯塔沙政权建立了约三十座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是号称“巴尔干奥斯维辛”的二战第三大集中营:雅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在天主会教士的积极支持下,乌斯塔沙政权还强迫塞族人改宗天主教(383-389页)。为此,塞族武装切特尼克(Chetnik,支持塞尔维亚亦即战前的南斯拉夫王室)采取了血腥报复,不过,1943年起,部分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沙达成了“和解”,甚至协助纳粹镇压游击队(Sabrina P. Ramet and Ola Listhaug ed., Serbia and the Serbs in World War Two, pp.185-187)。
弗兰采蒂奇和英灵军团
尤里·弗兰采蒂奇(Jure Francetic)上校是乌斯塔沙军事组织黑色军团(Black Legion)的指挥官,他也被认为是乌斯塔沙“精神”的最佳象征。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者罗里·约曼斯(Rory Yeomans)对弗兰采蒂奇做了研究,该文收录在丽贝卡·海恩斯(Rebecca Haynes)和马丁·拉迪(Martin Rady)主编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右翼人物的论文集《在希特勒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Hitler, I.B. Tauris, 2011)中。1930年代,弗兰采蒂奇在萨格勒布大学加入乌斯塔沙(论文集191页)。1941年,弗兰采蒂奇在萨拉热窝组建了乌斯塔沙第一团,以对付切特尼克和南共游击队。这支武装的目的,也是乌斯塔沙的目的,就是把懒洋洋的青年转变为无情的杀人机器。与前述乌斯塔沙意识形态相应,这些武装分子被设定成塞尔维亚“蛮族”的对立面(193页)。
|
|
《在希特勒的阴影下》
乌斯塔沙政权着迷于死亡和牺牲,他们的世界观以死亡崇拜为中心(197页),黑色军团自然惟命是从。黑色军团的纽带就是死亡崇拜,以及黑色军团的死亡叙事(198页)。黑色军团用宗教、神秘主义的术语描绘该组织的炮灰们,好像他们是基督教的烈士(同上页)。这个组织也特别崇拜男性气质,并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死亡崇拜(196页)。
黑色军团的另一个口号是“清洗”,清洗的对象则是“入侵”波斯尼亚东部,也就是生活在克罗地亚觊觎的那部分波黑领土(以德里纳河为界)上的塞尔维亚族人和波黑人(194页)。换言之,黑色军团进行了大屠杀。乌斯塔沙把“清洗”认定为民族“再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同上页)。人们不难发现,上述内容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质。
1942年12月,弗兰采蒂奇乘坐的飞机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击落,游击队的医生还给受了重伤的他做了手术,但没有成功。不过,直到第二年3月,弗兰采蒂奇的死讯才被公布。乌斯塔沙政权自然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天主教会也厕身其中。弗兰采蒂奇死后,他被任命为一支乌斯塔沙武装的指挥官(这支武装也以他命名),并被提拔为将军(198-199页)。乌斯塔沙士兵们甚至如此提问:“尤里会怎么做?”(203页)在这些活动中,时任乌斯塔沙武装头目安特·沃基奇(Ante Vokic)公开声称和弗兰采蒂奇的灵魂交流(200-201页)。乌斯塔沙政权如此装神弄鬼,把弗兰采蒂奇打造成不死之身,无非是为了激起武装分子的复仇情绪,并鼓动克罗地亚青年充当炮灰。1943年,右翼诗人弗拉基米尔·尤尔契奇(Vladimir Jurcic)写了首诗赞美弗兰采蒂奇(202页)。
余论:乌斯塔沙的当代回声
1945年,乌斯塔沙和纳粹一起灰飞烟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帕维利奇,以及前述雅塞诺瓦茨集中营首脑丁科·萨基奇(Dinko Sakic)等乌斯塔沙高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逃到了阿根廷。这些人并没有被他们的后辈们抛诸脑后。早在1990年,也就是克罗地亚还没有正式独立的时候,后来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Franjo Tudjman)就在反复使用乌斯塔沙的语言和符号,把乌斯塔沙说成“自决”,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1994年,图季曼访问阿根廷的时候,还冒天下之大不韪,会见了当时仍在人世的萨基奇。最晚截至2014年,克罗地亚仍然举行公开活动,纪念帕维利奇。
图季曼的后继者们延续了这个传统。今年3月份,现任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访问阿根廷,她说“二战后,许多克罗地亚人在阿根廷寻找自由的空间,他们的确找到了。在这里,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爱国”。虽然事后她否认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指控,但是2016年这位总统访问加拿大的时候,曾和乌斯塔沙旗帜合影,并将照片放上社交网络。这一举动,使得她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
|
现任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
纪念乌斯塔沙的活动不止发生在克罗地亚国内。1945年5月,在奥地利南部的布莱堡(Bleiburg)地区,南斯拉夫游击队杀死英军移交的约两万名乌斯塔沙武装分子和同情者,此外还有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分子、塞尔维亚土产纳粹利约蒂奇(Dimitrije Ljotic)的追随者,以及纳粹在斯洛文尼亚组建的武装组织本土防卫队 Home Guard——由于克罗地亚方面对布莱堡事件中死亡者的数字展开了一场“数字竞赛”,因此笔者这里采纳英国学者麦克唐纳提供的数字(David Bruce MacDonald, Balkan Holocaus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1)。1952年起,克罗地亚流亡人士就在当地举行纪念活动。克罗地亚独立之后,事件死者中的克罗地亚人自然就被特地挑出来,成了新政权眼里的“烈士”,他们的死亡也成了克罗地亚宗教保守派人士眼里的神圣时刻。除了2012年到2016年,克罗地亚议会都在资助这些纪念活动。可以想见,这些纪念活动中充斥着乌斯塔沙的旗帜和标志,成了他们的狂欢。在克罗地亚议会停止资助相关纪念活动的2015年,这个活动就是由上述那位在世界杯决赛后泪流满面的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资助的。
二战中的大屠杀问题是克罗地亚右翼的又一着力点。早在1980年代,前述那位图季曼就著书立说,极力缩小雅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罪行,并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进行污名化(图季曼的观点,及对图季曼的驳斥,见Tomislav Dulic, Mapping out the “Wasteland”: Testimonies from the Serbian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s in the Service of Tudjman”s Revision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23, No.2 pp. 263-284)。正如杜利奇指出的,图季曼就是为了对克罗地亚做民族主义动员。诸如泽利亚维奇(Zerijavic)等当代克罗地亚学者的手法与之大同小异。2016年,克罗地亚上映了一部声称雅塞诺瓦茨屠杀被夸大的电影,该国时任文化部长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Zlatko Hasanbegovic)对之大加赞赏。2016年底,克罗地亚右翼组织克罗地亚防卫力量(Croatian Defence Forces, 九十年代初期克罗地亚右翼政党的准军事组织)在雅塞诺瓦茨市放置了一块刻有乌斯塔沙口号的纪念碑。足足十个月之后,这块纪念碑被挪到了另一个地方。
|
|
纪念碑被挪动
上述行径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克罗地亚境内外的犹太人组织的警惕,他们多次谴责克罗地亚方面的相关行动。2016年4月,克罗地亚犹太人组织和塞族人组织拒绝出席该国政府举行的纪念雅塞诺瓦茨屠杀的仪式。2017年10月,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不仅仅是)克罗地亚的“大屠杀修正主义”。
不过,公平地说,对历史上右翼政权的美化和粉饰并非克罗地亚独有,而是中东欧各国剧变以后的普遍状况。1968年以后,中东欧各国的地下右翼民族主义就已经和各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们合流,右翼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血统和共同体,理所当然地指向了中东欧各国二战之前和其中的各路右翼政权。剧变之后,右翼民族主义在中东欧各国迅速死灰复燃,并借助社会经济危机的作用相继登堂入室,掌握大权。克罗地亚美化乌斯塔沙,塞尔维亚美化的则是切特尼克和纳粹傀儡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c,Ramet and Listhaug 前引论文集,Chapter 12&13)等。斯洛文尼亚右翼也在极力为前述的“本土防卫队”涂脂抹粉(Marusa Pusnik, Media Memorial Discourses and Memory Struggles in Slovenia: Transforming Memor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Yugoslavia, Memory Studies, 2017, 00(0): 1-18)。由于篇幅关系,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引用相关文献了。总之,剧变以后,社会经济危机,以及由社会经济危机导致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猖獗直至执政几乎成了适用于中东欧所有国家的公式。具体到克罗地亚,2015年克罗地亚的青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五(Fran Galetic, Lorena Skuflic et al., Economic Aspects of Croatian E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7 Oct., pp. 95-100)。克罗地亚乃至整个中东欧接下来将要走向何方,无疑是值得人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