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明: “幻灯片事件”之我见
作者: 廖久明
“幻灯片事件”之我见
在《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藤野先生》等文章[①]中,鲁迅毫无例外地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与“幻灯片事件”联系起来。直到21世纪初,绝大部分中国大陆学者都相信鲁迅的说法。日本学者却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的传记叙述中存在‘传说化’和‘虚构’,但并未直接否认《藤野先生》的纪实性自传性;20世纪60年代后《藤野先生》作为课文进入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与此同时,有关作品的认定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由诸如究竟有无‘幻灯事件’,何以弃医从文的讨论和解读,变成了对《藤野先生》的体式定性,即由自传性文章变成了小说。”[②]
尽管日本学者的观点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传入了中国大陆,“却很少被重视和利用,更没有被广大读者熟悉和接受”[③]。2005年以来,随着《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④](2005年)、《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⑤](2006年)、《鲁迅与藤野先生》[⑥](2008年)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和一些日本学者到中国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中国大陆学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仅罗列与仙台时期的鲁迅有关且提到“幻灯片事件”的文章):或者相信其观点[⑦],或者模棱两可[⑧],或者不相信其观点[⑨],或者未提其观点(其原因既有可能是回避日本学者的说法,也有可能是不知道日本学者的说法)[⑩]。为了重新树立中国大陆学者对“幻灯片事件”真实性的信心,更为了搞清楚事实的真相,笔者拟对日本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若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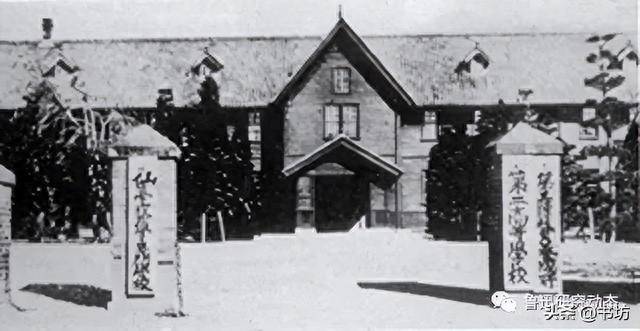
一、日本学者对“幻灯片事件”的质疑
通读译介到中国大陆的文章,可以知道日本学者质疑“幻灯片事件”真实性的理由有八个,现罗列如下:
一、没有找到鲁迅作品中描写的幻灯片:“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日俄战争时期,经常放映有关幻灯或电影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处决俄国侦探场面的原始资料,同鲁迅作品中的描写有所不同。笔者认为鲁迅所描写的处决俄国侦探的幻灯场面,是采取了夸张和虚构的方法,为的是强调说明日俄战争条件下,旅居仙台留学的鲁迅实现了弃医从文的转变。”[11]
二、三篇文章中描写的“处决方法”不同:“在《呐喊·自序》和《著者自叙传略》中的处决方法是斩首,而在《藤野先生》中却是枪决。”[12]
三、三篇文章中的“围观者”有差异:“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出现了围观者(中国民众),而在《著者自叙传略》中,却没有涉及围观者。”[13]
四、三篇文章中的“时间”不同:“《〈呐喊〉自序》写的是日俄战争时,上生物学课的课间。而《著者自叙传略》是日俄战争时的一个偶然的时间,《藤野先生》却是第2学年上细菌学课的富余时间。”[14]
五、三篇文章中的“地点”不同:“《著者自叙传略》以外,都明确写着仙台医专。”[15]
六、三篇文章中“医专学生的反应”不同:“《著者自叙传略》没有涉及。可是《〈呐喊〉自序》中写到,‘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藤野先生》中则强调了同学们全都拍手、喝彩,欢呼‘万岁’。”[16]
七、三篇文章中“关于鲁迅的看法”不同:“《〈呐喊〉自序》中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放弃了医学。《著者自叙传略》中写到了俄探处刑的事,日后就直接谈起提倡新文艺运动。《藤野先生》中则是富有小说式的表达,‘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17]
八、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同学记不记得是否看过中国人作为俄探斩首的幻灯片:“‘幻灯事件’的高潮是观众的鼓掌喝采和对此情此景不能附庸的‘我’的存在。在黑暗的映场,一个人听着一般看客对战争影片狂热拍手喝采的场面,只有剧场内的情景才符合。事实上的问题是周树人的同学之中没有一个人记得‘幻灯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家都证明‘拍手喝采’是不可能的。”[18]

鲁迅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冯雷摄
二、对“幻灯片事件”质疑的看法
现在,笔者逐一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目前虽然没有找到鲁迅作品中描写的幻灯片,中日学者却分别找到了来自同一底片的两张照片:中国学者隗芾以《关于鲁迅弃医学文时所见之画片》为题公布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的照片原载《满山辽水》画册,该画册出版于大正元年(1912年)十一月二日;日本学者太田进以《资料一束——〈大众文艺〉第1卷、〈洪水〉第3卷、〈藤野先生〉——》、《关于鲁迅的所谓“幻灯事件”——介绍一张照片》为题公布于日本《野草》1983年6月号、《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该照片“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但原载杂志弄不清楚”[19]。据太田进公布的照片的说明文字可以知道,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05年3月20日。鲁迅此时已来仙台半年时间,他离开仙台则是在一年后的1906年3月左右,也就是说,他完全可能在仙台看见该照片。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断定这两张来自同一底片的照片至少曾经出现在两种印刷品上:一、尽管这两张照片的主要内容相同,但是两边人物有多少之别;二、两处照片的说明文字不同。如此一来,鲁迅看见该照片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并且,鲁迅并不是完全没有看见由该照片制成的幻灯片的可能。中川爱咲的细菌学课(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微生物学,在《藤野先生》中所写的霉菌学)是从1906年1月开始的,接近一年的时间足以将该照片制成幻灯片并进行销售、放映。根据以下两个事实可以知道,我们不能因为东北大学医学系细菌学教室保存的15张日俄战争幻灯片中没有《俄国奸细之斩首》便否认它的存在:一、据调查,“在课堂上,时间有富余时,就让学生看日俄战争时局的幻灯”:“根据文部省‘忠君爱国、鼓舞节操’的精神,在学校放映时局幻灯是受奖励的(《战时地方教育上的经营》小册子1905年2月21日,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编集)。医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映日俄战争时局幻灯片的不太清楚,据鲁迅的同学说,好像是经常放映”;二、东京市浅草区并木町的鹤渊幻灯铺1905年1月6日在《河北新报》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出售俄国电影第2部15张,第4部20张,第7部30张,第8部30张”。[20]根据以上两个事实可以知道,当时制售了不少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鲁迅看过的幻灯片应该不止现存的15张。况且,即使鲁迅看的是照片而不是幻灯片,也不足以改变事情的本质:“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片不可。”[21]
二、《藤野先生》说日军处决中国人的方式是“枪毙”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照顾语感。鲁迅曾如此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22]可以这样说,“读得顺口”已经成了鲁迅的写作习惯。现在我们来看看该部分文字写到“枪毙”的三处文字:“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很明显,如果将第一处改为“我接着便有参观砍中国人的头的命运了”有些拗口。既然鲁迅凭语感在第一处写下了“枪毙”二字,那么在第二、三处写下“枪毙”便是一种顺笔而为的行为。由于鲁迅回到中国前后,不但看见过闲看枪毙的人,还看过闲看砍头的人[23],所以第三处的“枪毙”同时包含“枪毙”和“斩首”两种处决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枪毙”与“斩首”两个词在鲁迅作品中可以互换。至于具体的处决方式,可以肯定为“斩首”:首先,与“幻灯片事件”描述情况完全一致的现存照片《俄国奸细之斩首》显示日军处决中国人的方式为“斩首”;其次,《满山辽水》刊登的该照片的说明文字也证明了此点:“中国古来之刑,在于杀一儆众,故其刑极为严酷,宛如所见之佛家地狱图,毫不宽贷。若夫捕至马贼,游街之后,以所谓鬼头刀之钝刀处斩,裸尸曝市示众。尸体身首异处,横抛街头,血流凝聚成块,状不忍睹。/尤其日军对俄国奸细所处之极刑,多用斩首。今虽有废除惨刑倾向,但斩首之刑,目前仍存。”[24]正如说明文字所言,为了达到震慑的作用,“日军对俄国奸细所处之极刑,多用斩首”。
三、《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认为“幻灯片事件”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原因为:首先,日俄战争爆发的时间是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鲁迅是1904年9月初来到仙台的,也就是说,鲁迅到仙台一年后日俄战争才结束;其次,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相关报道结束,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定还有许多报道;其三,尽管“幻灯片事件”发生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幻灯片上的事情却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其四,鲁迅写作这两篇文章的时间是在事情发生近二十年后,记忆难免出错——《藤野先生》没有出错是因为只写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的时候而没有涉及到日俄战争。综合以上因素,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将“幻灯片事件”与日俄战争联系起来很正常。至于正确时间,则可以断定是鲁迅到仙台医专后的第二学年即1906年初[25]:不管是《呐喊》中的“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还是《藤野先生》中的“第二年添教霉菌学”都告诉我们,“幻灯片事件”发生时间是1906年初。据调查,鲁迅离开仙台前后的情况为:1906年2月下旬,鲁迅多次不来上课,个别要好的同学去看望并知道他要离开仙台;经常接触的四位同学铃木逸太、杉村宅朗、山崎喜三、青水今朝雄凑在一起,搞了个临时送别会,在米粉店或别的什么地方吃了点甜食之后,到照相馆拍了张纪念照片;后来,鲁迅不辞而别;3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李宝巽向学校发出鲁迅的退学申请书;3月15日,仙台医专批准鲁迅退学。[26]由此可知,鲁迅看见该幻灯片的时间很可能是1906年2月中下旬。
四、在笔者看来,三篇文章中的“围观者”、“地点”、“医专学生的反应”、“关于鲁迅的看法”有差异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三篇不同的文章,鲁迅有权根据其主旨决定哪些详写、哪些略写、哪些不写。
五、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同学的回忆不一定正确。(一)从事情发生的情景来说,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事情,只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才有可能留在记忆中。在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日本同学只是作为课堂余兴在观看,在观看中国人作为俄探被斩首的幻灯片时,只是作为日俄战争幻灯片之一在观看,这种情况很难留下深刻印象。从“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可以知道,鲁迅最初在观看时与日本同学并无多大差别,其原因应该与当时的日本是东方的代表而俄国是西方的代表有关。但是,在看见中国人作为俄国侦探被日军斩首的场景时,鲁迅意识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于是被强烈震撼,这种情况是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为了证明笔者的说法有道理,不妨看看鲁迅与藤野先生对“惜别”照片的不同记忆。鲁迅离开仙台前,藤野先生将一张背后写有“惜别”的照片赠送给他。1926年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时,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27]1936年鲁迅逝世后,当人们问及此事时,藤野先生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大概曾到我家来辞过别,最后的会面是什么时候,却已忘记了,一直到死还把我的相片挂在房里,真是让人欣慰的事,上面这样的情形,这相片照得什么样子,并在什么时候送给他的,也记不起了”[28]。值得庆幸的是,“惜别”照片还在,否则完全可能因为藤野先生“记不起了”而被人认为这又是鲁迅虚构的故事之一。(二)从回忆的情景上说,鲁迅的可信度更大一些。鲁迅是在没有外部环境干扰的情况下回忆的,他的回忆更有可能接近事实;鲁迅同学的回忆却是在证明一件重大事情是否发生的情况下回忆的,更有可能回避事实。(三)从回忆的时间上说,鲁迅的可信度也更高一些。鲁迅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写于1925年5月26日、《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它们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留下的印象应该更清晰一些;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的人员采访鲁迅同班同学的时间是1974年前后,此时距离鲁迅离开仙台的时间已经接近七十年,留下的印象应该更模糊一些。由于没有找到能够证明鲁迅说法的幻灯片,所以不能够能断定鲁迅的回忆是正确的。不过,因此认为鲁迅的说法是“虚构”、其同学的回忆却“正确”[29]的做法却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双方的回忆都存疑。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新岛淳良、吉田富夫都引用了鲁迅的日本同学的回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实际上都没有否认鲁迅看过中国人作为俄国侦探被斩首的场景:“大约周树人是在仙台的剧场里或某一个杂耍场里,作为观众当中独一无二的中国人看到了处死中国人的场面,他亲耳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鲁迅记述道:‘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30];“‘幻灯事件’决不是某一天在阶梯教室,即在细菌学课堂上的空余时间里所突然发生的事,而是在留学生周树人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事。”[31]笔者想说的是,既然鲁迅有可能在“剧场”或者“日常生活中”看过中国人作为俄探被斩首的电影或者幻灯片,那么,就对鲁迅情感的影响而言,它们与鲁迅在阶梯教室看幻灯片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三、对“幻灯片事件”质疑的质疑
面对日本学者的质疑,笔者觉得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鲁迅在当时会想到为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虚构这样一个故事么?二、这符合鲁迅的性格么?三、如果“幻灯片事件”是虚构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现在,笔者就结合以上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鲁迅晚年后声誉日隆,逝世后甚至被抬上神坛的地步,写作“幻灯片事件”前后的鲁迅的影响却并没有这么大。据与鲁迅有过深交的高长虹回忆,1924年9月底他到北京的时候,“周作人在当时的北京是惟一的批评家”,“直到《语丝》初出版的时候,鲁迅被人的理解还是在周作人之次”[32]。正因为如此,高长虹到北京后,希望结识的人是周作人、郁达夫。[33]不但此时的鲁迅影响有限,并且此时的鲁迅对自己也缺乏信心:《新青年》时期,早已意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他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是因为钱玄同的邀请[34],《新青年》的团体散掉后,他便“彷徨”起来[35]。在《呐喊·自序》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自己作品作价值的怀疑:“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36];“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37]。此时的鲁迅,绝对想不到人们后来会把他捧上神坛,因此虚构这样一个故事便于后人发挥。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他要虚构,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完全可以虚构得天衣无缝,以免给人们留下虚构的痕迹。实际情况则是,这三篇文章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被一些人发现后认为“幻灯片事件”是虚构的故事,这恰恰从反面正面它不是虚构的。
我们知道,鲁迅在和许寿裳探讨“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的时候,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38]。所以,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极力反对“瞒和骗”,主张“睁了眼看”:“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39]这样一个人,会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去虚构一个故事么?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么?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40]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不想太欺骗人”的目的,鲁迅不过是“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虚构。试想想,一个时时“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人、一个声称“我要骗人”[41]的人,他真的会骗人么[42]?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恰恰是那些声称自己从不骗人的人才最喜欢骗人。众多事实还告诉我们,鲁迅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43];“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奖金,还欠努力”[44]。所以,根据鲁迅诚实和淡泊名利的性格可以断定,他绝不会虚构这样一个故事。
笔者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幻灯片事件”是虚构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最终决定弃医从文?根据许寿裳的回忆可以知道,鲁迅与他讨论国民性问题的时间是“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的时候。也就是说,改造国民性实际上也是鲁迅选择学医的原因之一:“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45]既然如此,如果要改造国民性,鲁迅完全可以继续学医。他后来选择通过弃医从文的方式来改造国民性,一定是学医期间发生了重大事情。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不少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笔者粗略统计,除“幻灯片事件”外,人们还找到十多个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人们对这些原因的多数分析有道理,最终导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原因却是“幻灯片事件”:不仅因为鲁迅多次强调此点,而且因为“幻灯片事件”发生后不久鲁迅就离开了仙台。量变质变规律告诉我们,当量变达到质变的临界点时,一般需要一个偶然事件才能导致量变最终完成并达到质变,犹如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需要一阵微风来吹倒一样。“幻灯片事件”至少是这样一阵微风,使已经对学医意义感到怀疑的鲁迅最终决定弃医从文。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描写:“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46]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尽管幻灯片中的日军在砍中国人的头,鲁迅并没有写他对日军的不满,却非常详细地写了他对围观的中国人的不满,由此可知,鲁迅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这一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才使鲁迅在仙台那种特殊环境下看见该幻灯片时产生强烈震撼,决定弃医从文以便改变自己国家人民的精神。
综上所述,“幻灯片事件”至少可以做如下表述:在仙台期间,鲁迅在细菌学教室(也有一定可能是在电影院里或者日常生活中)看见“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斩首’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的场景(有很大可能是通过幻灯片看见的,也有一定可能是通过电影或者图片看见的),受到强烈震撼,“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鲁迅最终决定弃医从文,于是离开仙台,前往东京。

对鲁迅,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曾经将其捧上神坛,一切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这种做法很明显不对。不过,多数日本学者研究“幻灯片事件”的做法同样不可取:由于一些细节问题便不相信鲁迅反复强调的说法,甚至对与鲁迅的说法完全一致的照片《俄国奸细之斩首》视而不见或者轻描淡写,却想方设法去证明鲁迅的说法是“虚构”的。在笔者看来,研究任何一个对象都应该如陈寅恪所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47]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既不匍匐于研究对象的脚下,也不凌驾于研究对象的头上,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