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
2025-03-23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县境内的“自治”,不是“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例子,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主权。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端口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从权力构成上来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地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与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就明白“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与“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与耆英那样敷衍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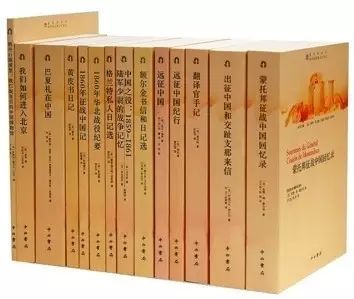
英法联军的士兵中,本来许多是华人。……据《庚申夷氛纪略》说:英法联军“在粤招募潮勇,传言不下二万人。潮勇者,潮州之无赖游民也。又募发配在粤之遣犯,多系川、楚、登、莱之人,得数千,皆亡命之徒。又有一种名青皮者,即失业粮船水手,性素犷悍,亦相聚万余人。每战则令遣犯、青皮当先,潮勇次之,而白黑夷殿后”。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下令关闭所有北京城门。说来奇怪,他们害怕的并不是英法联军,而是清朝自己的“败兵”。“兵败如山倒”,“伤兵老爷”最霸道。初七日,北京城门关闭,“闭门者,恐败兵一拥入城,又恐蒙古兵入。城内立即纷纷,东城尤甚,南北小街一带,买米、买面、叫煤者,盘旋如蚁,人声鼎沸。是日,出城听戏、送殡者,均关于城外”。如此害怕“自己的”军队,可见清朝的“内乱”有多严重。“趁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一个市民中间阶级,个人没有独立的财产、事业和追求,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也不懂得尊重别的任何东西,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
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的内情里,原则并非重要,它只是相互攻击的借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
“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的残酷结局而告终; 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 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