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的日语殖民问题
来源:伪满洲国研究中心
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采取脱亚入欧的现代化策略,强烈地学习和化用西方的现代技术、西方的现代制度与现代思想;同时也自觉地抵抗一个被日本意识化的西方,但它最终还是想象自己能成为西方国家一样的国家。通俗地说,日本对西方“既恨又爱”,或许准确地说是不得不既恨又爱。那么一个后发的亚洲国家何以可能抵抗那强大的西方呢?日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在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其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中国与日本在亚洲格局中的关系。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还是亚洲的“老大帝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让日本看到了重新布局亚洲的希望。1895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在亚洲殖民的野心。从1895年到1945年这半个世纪,是日本现代化最为疯狂的年代,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最为猛烈的年代。
如果说日本对西方既爱又恨,那么对中国就是既恨又爱。同样是爱恨交织,趋向却不太相同。日本脱亚入欧的道路是在被西方国家逼迫之下的主动选择,但其最终目标是成为西方式国家。日本迫切要求摆脱中国文化的种种要素,特别是日语中的汉字,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过程中,大量采用汉字以铸造新词对译西方学语的行为,又无疑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元素。

柄谷行人,日本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借用柄谷行人的“内面”说法,不妨把“国语-日语”的想象与建设视为日本现代化以及殖民侵略史的内面的重要因素。子安宣邦、小森阳一、李妍素等日本学者对日本的近代国语进行过深入的批判。日本近代“国语-日语”的想象及建设与日本殖民侵略的进程具有共同的步伐和节奏,成为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国语的概念在明治早期是没有的。它的概念和构成是随着日本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步伐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日本“国语-日语”殖民意识形态性质并没有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而结束,警惕并清理这种意识形态的道路还很漫长。“战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语意识形态的终结。国语,曾经作为殖民意识形态基础的一部分,即使在日本失去殖民地之后也不会死亡。”近年仍有日本学者认为,日语从古以来从文字到发音都受到汉语汉字很大的影响,“只有通过排除掉这一切,才能描绘出本来的日语面貌。”
萨特对欧洲殖民主义有过猛烈的批判:“扫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替换他们的语言,破坏他们的文明,却不给予我们的文化。”罗伯特扬把这概括为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非人类化”。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竭尽全力用八紘一宇的思想钳制中国人,竭力把日本语作为伪满洲国的国语而实行殖民统治,只不过是达到快速殖民的效果。殖民者永远不可能给予被殖民者平等和权利。
1
日语:殖民工具与殖民意识形态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通过控制伪满洲国这一中间机关而实施殖民行为,这一情形与日本在台湾和朝鲜的殖民形态不一样。1936年随着伪满洲国新学制的推行,日语被作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之一而得到推行,日语和满语(即汉语)成为伪满洲国的国语。“日语”、“日本语”和日本的“国语”这几个词语的意思如果不做细致的区分,大致也指同一个对象,但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日本语”与日本的“国语”之间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在此不能对这段历史做细致的梳理,只关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语和日本的国语如何被作为殖民工具的。
山田孝雄曾在《何谓国语》(1941)中写道:
我们所认识的国语乃是作为日本帝国核心的大和民族发表思想和理解的工具,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使用这个国语,未来也将以此向前迈进的。这个国语发源于大和民族之间,是大日本帝国国民的通用语言,简而言之,即大日本帝国的标准语。这里所谓的标准语意味着它是作为国家统治上之正式语言,并且是作为教育上之正式的标准语言。
同样在1941年,安藤正次在《日本语的输出和日本语教育》(1941)中写道:
日本语对东亚诸国的输出……恐怕只是作为一种外国语而存在的吧。不管我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怎样得到巩固,我们脑子里仍要清楚,日本语的输出是作为东亚共同语而输出于诸国的。……必须注意到,东亚共荣圈作为共同语之日本语的输出,对于我国之外的东亚诸国来说,只是在吸收一种外国语。
综合起来看,“国家内部”之“国语”(kokugo)以其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而强调其作为“东亚共同语”之“日本语”(nihongo)。日本内部的“国语”与输出的“日本语”达到了一致。
第一,在伪满洲国,日本语被赋予无上的优先性。东北沦陷后,日语作为殖民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一部分,被不断强化。《满日议定书》的最后一条为:“本议定书、缮成汉文日本文各二份、汉文原文与日本文原文之间、如遇解释不同之处、应以日本文原文为准。”在法律条文的阐释上,日本文的优先地位明白无误地确保日本殖民意识的贯彻,同时也确立了日本语的优先性。
日本语的优先性不仅在法律条文上得到保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鲜明的症候。刊于《同轨》第1卷第9期的《学习日语的急务》一文表示:“由满人的立场说,学习日语实比任何一切都切要,无论在根本问题或业务的现实问题,又我等将来的生活现实,若忽略了此事,便是一切皆失其根本而背驰于现实状势及根本精神。”日语对满人的重要,一则表现在现实的或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上,更重要的是日本殖民的那个“根本精神”。这里三次出现“根本”一词,都指向所谓日满亲善的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观念。
与之对照的情形是,日本人对汉语极不重视。根据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的考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把中国语当做“胡同里的外语”,外交官员中也只是低级官员才懂中国语。他的根据之一是仓石武四郎写于1941年的《中国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驻在北京或南京的官员,中国话说得好的大多是低级官员。在官员的提拔以及影响力上,欧洲语的修养受到极大的重视,而中国语则无足轻重。安藤彦太郎还指出,仓石武四郎(1897-1975)、藤堂明保(1915-1985)、竹内好(1910-1977)这些以研究中国学术著称的日本学者在大学里都没有学过中国语。日本的中国语教师让学生背诵《急就篇》,学生询问文法时,教师大喝一声“中国语还有文法吗!”因此,可以推测蔑视中国语(汉语)的情形在日本人中极为普遍。山田孝雄在《国语中的汉语研究》(1940)中把汉语当做日语的入侵者。其实,汉字是日语内在部分,没有汉字就没有日语。子安宣邦反对本居宣长阐释《古事记》时对汉字做出的排斥性做法,即仅仅把汉字当做表音记号的异质性存在。子安宣邦认为正是汉字的存入,日语的书面语才得以成立。日语中存入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表音记号的存在,还是一种认知意识的存在。比如《古事记》开头“天地初发之时”中“天地”怎么读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了汉字“天地”,“其神话式的起始记述才成为可能”,意味着一种表达方式的可能,一种认知方式的可能。日语书面语的成立是日本生活的一大飞跃,继而可以说,“随着日本书写语言的成立,日本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语言·日语也成立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汉语汉字的轻蔑同时也意味着对日语的轻蔑,这就显示出山田孝雄等人轻视汉语汉字的荒唐可笑。
第二,日本语被规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1936年伪满洲国推行“新学制”,“新学制”的教育方针彻底显示了新学制完全是为殖民侵略服务的。《学制要纲》第一款“教育方针”:“基于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趣旨、除体认满日一德一心不可分关系及民族协和精神、深明东方道德——尤其是忠孝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外、并以安定国民生活必要之实学为基调、授以知识技能、以谋增进身体健康之保护、以养成忠良国民、为教育方针、”(标点原文如此,已经校对)《学制要纲》第三款“学制立案上之要点”中第六条为“日本语基于满日一德一心之精神、重视为国语之一”。(标点原文如此)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日本语“重视为国语之一”,即日本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之一种。这样,日本语与满语(满语即汉语,是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故意把汉语说成是满语)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国语。第二,日本语的目的在于传播“满日一德一心之精神”,因此,日本语就不只是一种表达交流的自然性质的工具,而是成为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载体与基础。“一德一心”来自八紘一宇的思想,把全世界当作一家而加以统治。八紘一宇即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溥仪在东京审判会上说“日本是一德一心要把满洲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对“一德一心”的使用表明他对日本殖民者的愤懑与讽刺。
新学制的特点在于,“重视作为国语之一”的日语。日本在1937年3月10日文教部训令第26号就命令各学校讲授日语,把日语作为“国语”讲授是从“新学制”开始的。在《国民高等学校规定》第四条中,明确规定国语学科为“日语及满语(即中国语)”或“日语及蒙古语”,每周授课时间为日语6小时,“满语”3小时。对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对于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在综合学科的“国民科”中讲授“国语”,规定日语周授课时间为6-8小时。李昌毓(1924-2002)积极参加星火读书会,主编《大地》油印刊物,回忆1940年在盖县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情景:
星期一在大礼堂举行朝会,全体师生参加,礼堂正面是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旗,先唱日本国歌,后唱伪满洲国国歌,由校长用日语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再由教导主任用“满语”(即汉语)宣读。
为了实现日本语作为伪满洲国“国语”的目的,伪满文教部刊出《关于在学校教育上彻底普及日本语之件》,其内容为:
为令遵事查本部为使学生体认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不可不图日本语之彻底普及兹规定具体办法于左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省长转饬所辖各学校或县市长对管内各学校一体遵照办理此令
计 开
一、日语教师在教授日本语时不仅练习语学须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及风俗习惯以努力发扬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为要
二、使教职员及学生理解日本语普及之重要性
三、学校教职员必须励行学习日语
四、教职员及学生在学校内应奖励使用日本语在家庭亦于可能范围内奖励使用之
五、日人教师在教授他学科时亦应斟酌使用日本语满系教员如略解日语者亦于可能范围内勉励使用之
六、须利用各种机会以引起日本语学习之兴趣
七、举办学生日本语演说、演艺等会
八、以学校为中心举行一般民众日语讲习会
九、在满文上使用之学术名词于可能范围内须与日文相符(原文标点如如此,已经校对)
2
“同文同种”:魅惑与虚幻
在中日关系的叙说中,“同文同种”是一个极具有魅惑性的词语。以“同文同种”为关键词形成的话语都必须重置于历史语境中接受话语分析的检视,方可确定其意义。在自然状态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属于黄种人,因此说“同种”是毫无问题的。日语借用许多汉字,日语的字母平假名和片假名也从汉字的偏旁和书体中化出,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文”大致也可行。但就谱系学观点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一说),并不“同语”。“同文同种”这一观念并非东北沦陷后才有,也并非只有中国人才有。比如日本人宫崎安藤的《日清英语学堂记》(1898)就曾经提出“日清两国,同文同种,同处于亚洲,辅车相依,自古兄弟之国”的看法。然而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者和某些中国人所宣扬的“同文同种”观被烙上日本军国主义鲜明的殖民印记,同时也画出了伪满洲国时期某些中国人的奴性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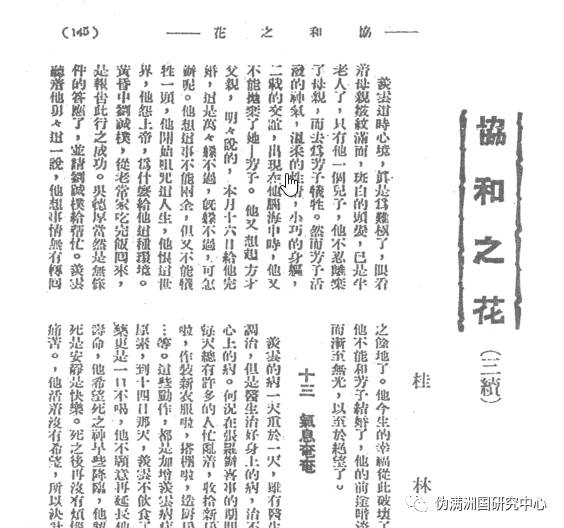
《协和之花》,原载《新满洲》第1卷4—6期
署名“桂林”的作者在《新满洲》第1卷第4期至第6期所发表的小说《协和之花》 是一篇典型的宣扬“同文同种”的作品,露骨地表现了奴化之心与谄媚之意。故事的梗概是:中国人吴羡云和日本姑娘中村芳子在伪满洲国相恋,后芳子回国,吴羡云考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吴羡云与芳子姑娘回到伪满洲国,两人结婚。
吴羡云考上日本留学生,写他第一次到日本的情形与心理:
他经过工商要府的大阪。历史名地的京都。赏玩过代表友邦的樱花。瞻望过高耸云表的富士山。这样以来,如此长途旅行,并未感到寂寞,四月二十七日早七时,车抵东京驿,这时吴羡云心理,真是兴奋到极高峰上去。忙提着手荷物,随着人群往外走。“吴さん!吴羡云さん!”的呼声传到他的耳鼓……
日本风景的展示、协和语的运用(如“东京驿”、“手荷物”等)与吴羡云“兴奋到极高峰上去”的心情融为一体。“大阪”、“京都”、“樱花”和“富士山”,这些风景成为被殖民地人来到宗主国的发现,意味着宗主国的美丽,而那以“吴さん!吴羡云さん!”的日本语再次出场的日本姑娘则成为风景中的风景,美丽中的美丽。叙事者的赞美同时也是作者的赞美,因为整篇小说的叙事意向表现为叙事者与作者的高度一致。小说以大团圆结局收束,吴羡云与中村芳子结成夫妻。小说借用他人之笔对此婚姻进行赞美:
康德六年一月十日,羡云原籍某汉文报纸登出了一段,如左的协和佳话。略云,东京特派员函,日满两国,同文同种,乃唇齿相连之邦。共存共荣,成不可分离之势。然为两国之百年亲善计,彼此通婚,正为不可少之事。今将日满两国。所乐道之一段协和佳话记之如左。并祝协和之花畅开乐土之果早结。……吴君言,此为其素日宿(疑为“夙”字之误——引者)愿,一旦得偿,不胜喜悦并谓将来,必为日满两国协和上,尽以全力,且归国后,从事于教育事业云云。(已经校对)
“康德六年一月十日”的纪年符号是鲜明确定的伪满色彩。“汉文报纸”登载着“协和佳话”的配置具有某种暗示性,因为这段“协和佳话”为“东京特派员”所写。于是暗示性由此得到明示:“日满两国,同文同种,乃唇齿相连之邦。共存共荣,成不可分离之势。”“同文同种”所结成的“唇齿相连之邦”无疑是被当做“共存共荣”这一“不可分离之势”的基础看待的。
“同文同种”成为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话语与伪满洲国被殖民话语的一部分。有自称“新民”的人在《建国弹词 日满亲善》中写道:“同种同文同帝国 提携永固天地长。”伪奉天省省长金荣桂1939年给《同轨》的新年题词为“同文同轨,促进亲善”;赵鹏第题词为“同文同轨,一德一心”。大东文化协会编《标准支那语教科书》(卷三,1941)的第十四课《善邻提携》:
在日本西方,隔着一条大海,和我们兄弟相称,患难相共的好朋友,那就是中满两国。他们本来和我们同一民族,皮肤是黄的,眼睛和头发也是黑的,性情习惯以及文字文物,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儿,彼此同样的尊孔拜佛,那国,原来是地大物博,人口的八成都市种地的,可是他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苦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他们几个军阀和党人们,不知东亚大局的实情,暗招私兵,滥征重税,抗争势力,内乱不绝,这是他们农民,受苦的大原因哪。可不是么!事变以后,那两国的内外情形,都更新面目,百姓们的享福,也就快实现了。就是就是。
上述三个例子,分别为个人抒怀、官僚题词、教科书课文,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同文同种”是“日满亲善”的基础,能促进“日满亲善”,能结成“一德一心”,因为同文同种所以日满亲善有了根基。这样的后果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意识转化为自殖的意识。伪满洲国的中国人宣扬“同文同种”显然不过是奴化的表现。
同文方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满语カナ(即满语假名)”的出台。满语假名的方案,最早由伪满洲国大同学校的中国籍教师曾恪于1934年提出,1937年“伪满洲国”协和会组织座谈会得出认可的结论,1940年伪满洲国国语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满洲假名的实施方案。1934年曾恪的《满洲国语音标》提出了满语假名的设想。
曾恪在中华民国注音字母与日本假名之间,选择后者作为伪满洲国国语(即汉语)的音标。其所制满洲国语音标方案,计字母81个(因ィェゥ三个假名重复,实则78个),韵符13个,声符61个,两用符4个。 “满语カナ”“就是用日本的カタカナ表出满语(汉语与汉字)的声韵。”满语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满语カナ拼音表》,分满语语音21个声母,36个韵母,408个基本音.满语カナ拼的都是北京音,但是拼音符号采用日语假名。
曾恪提出采用日本假名的四点理由:
一、日本假名。本由汉文改造。在东洋已有极大势力。尽可利用。何必标新立异。另创新符号。
二、日本假名。若改为国语音标。 读法百分之九十。一仍其旧。只声符特加一行。韵符改定数字而已。日满二国。均可通用。益见同文之美。更昭协和之庥。
三、与中华民国之注音符号较。字母虽多。但介音可省。两拼者多。三拼者少。似繁实简。
四、满洲人以此为阶梯。易习日文日语。日本人以此为阶梯。易习汉文汉语。语言同化。逐渐可期。(已经校对)
晚清以降,中国人主动借用日语假名、罗马拉丁字母以创制汉语拼音符号的尝试并非不可,但曾恪所为,放弃1930年代已经通用的中华民国注音符号不用,同时也不采用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而坚决采用日语假名作为汉字拼音方案,其目的落实在“益见同文之美。更昭协和之庥”。曾恪的观点也得到个别人的呼应,比如何云祥的《满语カナ及其创制之意义》一文先花了大量的笔墨论述文字的重要,无非是为满语假名的出现做铺垫,最后把满语假名的效果落实在伪满洲国和大东亚上:对于伪满洲国,对于大东亚的前进,满语假名的功绩不亚于“几百万启罗瓦特的电气”、“几千万盹的石炭”。满语假名的出台,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方式,也是伪满洲国时期具有奴性的中国人自我殖民化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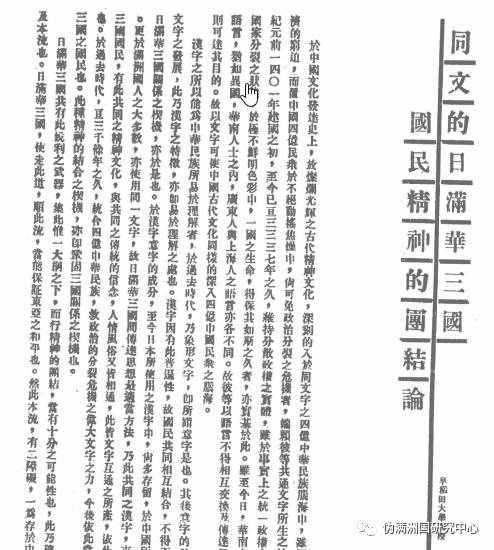
《同文的日满华三国国民精神的团结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11期
日本如何看待同文同种,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的《同文的日满华三国国民精神的团结论》:
汉字之所以能为中华民族所易于理解者,于过去时代,乃象形文字,即所谓意字是也。其后意字的及音字的两成分合成文字之发展,此乃汉字之特征,亦即易于理解之处也。汉字因有此普遍性,故国民共同相互结合,不得不谓此也。申言之,日满华三国关系之契机,亦于是也。于汉字意字的成分,至今日本所使用之汉字中,尚多存留,于中国所使用者,亦多残在。更于满洲国人之大多数,亦使用同一文字,故日满华三国间传达思想最适当方法,乃此共同之汉字,东亚民族中之日满华三国国民,有此共同之精神文化,与共同之传统的信念,人情风俗又皆相通,此皆文字互通之所产,依此今后当得而发扬之也。于过去时代,亘三千余年之久,统合四亿中华民族,救政治的分裂危机之伟大文字之力,今后依此当可继续结合日满华三国之国民也。此种精神的结合之契机,亦即巩固三国关系之契机也。
日满华三国共有此锐利之武器,集此惟一大纲之下,而行精神的团结,当有十分之可能性也,此乃确保东亚和平之本道及本流也。
使日满华三国精神的结合之力,乃亘三千余年结合四亿中国民众之结合契机,即汉字是也。
今者各种障碍著著破除,日满华三国国民之精神的结合契机,三国关系()[看不清楚]整之大纲,厥为汉字是也。
日本殖民者的“同文”是一种殖民方式,作为殖民话语具有强大的魅惑性,因为它抓住了汉字这一共同符号。
日本殖民者的“同文”话语的分裂性在于,对伪满洲国人高呼“同文”乃是日满亲善的基础;但是在内部却非常轻视所谓同文的汉语汉字。伪满洲国的人的“同文”乃是一种自殖的方式,作为殖民话语的呼应话语具有强烈的趋魅性,成为自我殖民的符码沉溺。
再来看同种方面。《协和之花》结尾处赞美吴羡云与中村芳子的婚姻,“并祝协和之花畅开乐土之果早结”。“乐土之果早结”不过是中国人“早生贵子”祝贺语的另一种说法。在此是对“同种”的诠释。当然更重要的是,“乐土之果早结”的目的在于“日满两国协和”,吴羡云与中岛芳子的恋爱、婚姻和生育都打上了鲜明的殖民印记,成为殖民的意识。
小说对中岛芳子的刻画值得关注。小说结尾部分引用中村芳子的日记两则。中村芳子的这本日记被她作为爱的纪念品题名《别痕愁迹》。所选两则日记的第一则记于“七月七日 月曜日”,以中国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表达思念吴羡云之情。其中提及学习满语的情况,因无心学习满语而放弃一段时间,决心从第二天开始继续学习满语。第二则记于“九月十五日 火曜日”:
九月十五日 火曜日 今天是我国承认友邦满洲国的庆祝日。在学校举行完毕庆祝典礼,大家叫我讲演关于满洲国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风俗人情。讲了一些。末后并把满洲国男子的优点,讲了不少。她们都说我讲的太详细了,其实我是单为着我的云哥。可笑的是山田梅子。竟来求我给她介绍一个满洲男子。我先假装推辞不行,后来她诚恳求我。加上我俩感情很好,所以答应她了。(已经校对)
中岛芳子介绍“满洲国男子的优点”与日本国家“承认友邦满洲国”同位于殖民的链条上,其方式和功能是同构的。但又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层面下降和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生育上,让殖民变得平常普通和富有人情意味。
但是,作者“桂林”对日本姑娘中岛芳子的想象只是殖民地自我奴化的人的一厢情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久殖民东北的目的,曾经搞了个“拓殖”计划,即把日本人移民到东北来。那些被鼓动为了“拓殖”任务而到东北来的未婚姑娘被称为“大陆新娘”。有学者已经指出,大陆新娘的任务是成为使移民定居的工具,增产农产品,提高人口出生率,增加在满洲的大和民族的人口;以女性的温柔压制当地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使民族融合政策获得成功。等等。
日本的《女子拓殖指导者纲要》向“大陆新娘”提出四项要求:
第一,为确保民族资源,首先须增强开拓民的定居性;第二,数量上确保民族资源的同时,须保持大和民族的纯血统;第三,将日本妇道移植到大陆,创建满洲新文化;第四,在实现民族协和方面,有许多地方需要女性的配合。
“强调大和民族的纯血统论,女性必须成为‘血液防卫部队’”。由此看来,日本殖民者反对日本的“大陆新娘”与中国人通婚。中岛芳子对伪满洲国男人优点介绍,她与中国人吴羡云的结合,不妨看做是作者“桂林”对日本女性的虚幻的想象,虚幻的基础是被殖民的人们对于殖民国家异性的渴望。
满语假名方案的制定以达到“文”的融合,《协和之花》中吴羡云与中岛芳子的结婚以实现“种”的融合,这些都不过是“同文同种”这一殖民魅惑性话语的演绎。对于伪满洲国的人来说,这只是殖民压迫下自我殖民化的症候。对于日本殖民者而言,这只是所有殖民国家对待殖民者人们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日本殖民者在自己内部根本不认同“同文同种”。他们歧视中国语,歧视中国人。他们之所以会对伪满洲国的人宣扬日满两国“同文同种”,不过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人们惯用的一种话语策略,正如萨特对西方殖民国家的人道主义所批判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谎言的意识形态,对于劫掠的完美辩护;其中的甜言蜜语及爱心都不过只是我们侵略的借口。”
3
“协和语”与自我殖民

《语言导论》,[美]维多利亚·弗罗姆金著
从语言类型的归属上看,“协和语”属于洋泾浜语(pidgin),而不是克里奥尔语(creole)。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大多是因为战争与殖民使得生活在被殖民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的语言形式。洋泾浜语不同于克里奥尔语。美国学者维多利亚·弗罗姆金和罗伯特·罗德曼在《语言导论》给出了区分两者的标准:
第一,洋泾浜语言的区别特征之一是没有一个人把它作为本族语来学习。当洋泾浜语被某个社群采用作为他们的母语,儿童们学习它是作为第一语言学习时,这种语言被称为克里奥语。
第二,洋泾浜语发育不完备,而克里奥语是发育完备的语言。
“协和语”没有被任何人当做母语来学习,它也不是体系完备的语言,所以它属于洋泾浜语而不是克里奥尔语。协和语“绝不是有体系的语言,可以说是语言迥异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迫于日常意识的沟通的必要而诞生的一种洋泾浜(pidgin)语。” “迫于日常意识”暗指“协和语”的诞生以及历史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殖民的历史有着密切关联。“协和语”的出现并非始于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的出现,在之前有它的形态,如晚清时期的“大兵中国语”。但相比之前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其他沦陷区而言,它最活跃的地方无疑是“伪满洲国”。“协和语”这一名称也许得之于“五族协和”的提法。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透彻,我必须引入一篇小说——张毅的《咖啡女》。故事的大致内容是:小说的叙事者和主人公——“我”(署名大卫),是“满映会社”剧本员,作家,绅士青年,是中国人。他所读的书刊有《新女大学》《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满洲电影的方向问题》等,在帝都大新京(长春)爱上亚拉拉茶店一位咖啡女——娜娜——哈尔滨来的混血姑娘,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协和语往往作为人物语言出现,不作为叙述语言出现。但《咖啡女》的叙述语言却喜好用协和语:
“在受付处,我为她报告名,在受付簿上,我替她写上一个假的名字……‘西村淑子’,二十一岁……”
亚拉拉的服务规则是那样的,每一个姑娘都是轮流在二阶勤务一星期,现在是娜娜在二阶勤务的一周间。这一周间的二阶勤务,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方便,双方都因为拘束较少,所以说什么来也比较自由。
第二天,我带着会社的案内书与演员写真帖到宝山去。
小说的叙事者使用协和语来叙事很自觉,似乎在享受使用协和语叙事的快乐与满足。表面看,协和语叙事只是一种叙事方式,但内面却蕴藏着叙事者“我”幻想女主人的独特方式,即协和语叙事不断把女主人公娜娜日本化和协和化。“我”对女主人公有两次命名。娜娜不是女主人公的原名,是“我”给女主人公第一次命名的名字:
我起初不相信她是满洲女性。
陈云裳一样的华丽,陈燕燕一样的温婉——我不能不注意她了。
“娜娜”是我后来给她起的名字,她本身就像这个名字一样热情而富有魅力……

《娜娜》,法国作家左拉长篇名作
娜娜,更容易让人想到法国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中的女主人公娜娜。《咖啡女》中并没有明说这一点。男主人公兼叙事者的“我”是一个小资情调很浓的青年。他喜欢看电影,喜欢文艺作品。左拉笔下的娜娜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成员,出身低微,但长得性感,成为红极一时的交际花。她热情似火,情欲旺盛,挥霍无度,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但又善良坦诚。“她本身就像这个名字一样热情而富有魅力”这句话不妨看作是左拉的《娜娜》中娜娜的写照,同样也是《咖啡女》里娜娜的写照。娜娜虽然是咖啡店侍女,但并不是卖淫女。“我”看中的是她的热情而富有魅力。“我”退掉与大连姑娘的婚约,准备过一种孤独的寂寞的单身生活,相信“孤独与寂寞是灵魂上的一种寂寞与美”,但爱上亚拉拉茶店的娜娜。娜娜是一位混血姑娘,父亲中国人,母亲俄罗斯人。这种民族身份和职业身份都被看作是低等的。那么“我”爱上娜娜这件事情本身似乎有着政治的抵抗意味,但是整个叙事语调显示,叙事者并没有把这种意味稍稍注意,当然可以归之为伪满洲国的高压的时代语境,相反,“她以为我是日本男子,正像我以为她是日本女性一样,她起初之对我,也等于普通的日本客人是一样。”他们把对方想象为日本人的意识彻底消解了上述抵抗的意味。
“我”第二次给娜娜命名,是“我”把“娜娜”改名为日本名字——“西村淑子”。给一个中国人强行安上一个日本名字,这是否可以看做协和语的一种变体?不管怎么说,小说给娜娜日本名字,无疑是在把娜娜日本化和符号化,同时以协和语为中介把娜娜虚幻化。也许有人以为小说给一个咖啡店的侍女一个日本名字(“西村淑子”这一日本名字在日本语境中是否有独特的含义我不清楚,比如是否与历史上某位女性有关从而暗示某种独特的意义等等。)无疑是一种反讽,但是从小说的叙事语调来看,完全看不出反讽的意味。叙事者在以协和语把娜娜日本化的过程中似乎还得到一种享受。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娜娜时就以为她是日本女性,而在约会中把娜娜想象为日本贵族小姐。写“我”在宝山吃茶店见到娜娜的情景:
谁还敢轻蔑的以为娜娜是吃茶店亚拉拉的姑娘呢?她在这天,穿着红呢(原文如此——引者)的秋大衣,戴着俄国式姑娘们的红呢毡帽,黑色的遮光眼镜,白纱的呼吸囊。……如果我事前不曾约定了她,则在这即便是遇到了,那我也不敢冒然的,便以为(怀疑丢了一个“不”字,因为与后文的文意不符合)她便是在吃茶店亚拉拉认识的姑娘,而以为她是一位纯粹洋化了的日本贵族小姐。
“纯粹洋化了的日本贵族小姐”,意味着日本女性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时尚性与贵族性的完美结合。
《咖啡女》中协和语叙事把娜娜日本化、符号化的过程,足以彰显小说中“我”这类伪满洲国的人自我殖民与自我奴化的无限膨胀,协和语成为自我殖民与自我奴化的深渊。通过协和语叙事完成的对日本女性的完美性的程度越高,则伪满洲国中国男人的自我殖民与自我奴化的意识就更深。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