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大上异军突起的彭述之
作者: 张东明
彭述之是谁?有多少人知道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后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实的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这颗中共四大产生的政治新星为何如流星般划过上空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位中共早期的活动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
季诺维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苏三领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家乡离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过十数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俄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彭述之著作颇丰,口才也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在苏期间,他担任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很受重视,连苏俄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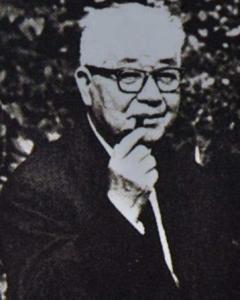
◆彭述之
留学莫斯科期间,彭述之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同年8月,彭述之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与《新青年》杂志。因为直接受陈独秀的领导,逐渐成为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
中共四大上的重要人物,地位直线上升
1924年12月初,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即他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述之与陈独秀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二者并无分歧;维金斯基则持异议,他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维经斯基也承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观点。
在这场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到底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彭述之认为“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他批评中共“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此之前,彭述之曾专门为《新青年》撰写了一篇文章《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客观地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
在产业工人能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彭述之也是支持的态度。据他本人回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会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大会审查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关于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大会最后选举了由9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彭述之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后称部长),后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后,暂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国,张国焘经常不在上海,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便由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据彭本人回忆:“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可见,其筹备、参加中共四大确是辛苦。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他对未来党的前途充满憧憬:“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900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1000党员,并且党员中公认已占50%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直到晚年于海外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向导》周报的主编,拒绝刊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时期,《向导》周报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作为党内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彭述之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陈独秀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毛泽东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陈独秀将之搁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瞿秋白的争取下,3月12日,《向导》周报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还不许《考察报告》在《向导》上继续刊登。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陈独秀路线的拥护者,最终分道扬镳
1926年是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作为中共当年主要领导人之一, 彭述之深深地陷入了旋涡之中。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了著名的 “中山舰事件”。为反击蒋介石,限制他的权力的膨胀,陈独秀召集中央会议,决定采取四条对策,其中之一是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六人组成,彭述之为书记。陈独秀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派彭述之与妻子陈碧兰带着中央批示坐船从上海去广州落实。
几乎就在同时,广东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于4月29日带着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回到了广州。鲍罗廷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一位传奇人物,1923年9月,鲍罗廷作为苏俄政府和苏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的代表到中国,不久被孙中山先生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权力极大。当时,苏共中央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坚决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后者占了上风。彭述之关于共产党集体退出国民党的方案还没有实施就遭到鲍罗廷的压制。鲍罗廷甚至提出:此时此刻“共产党员应该是国民党的苦力”。彭述之广州之行一无建树,只好带着陈碧兰于6月初悻悻返回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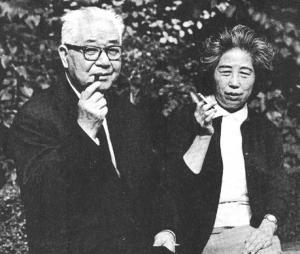
◆晚年彭述之与陈碧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但是陈独秀和彭述之依然抱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对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变通和驾驭的能力。中共中央执委在上海召集一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北伐。陈独秀提议反对北伐,彭述之随即表示支持。但执委中张国焘和瞿秋白反对,最后进行表决,以2票对2票不相上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赞同北伐。这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1926年底,苏联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华,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在武汉与鲍罗廷商议后,一致认为中共党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要中共党内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撰写文章,反对陈独秀路线。正如这三位苏联代表1927年3月递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换领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对彭述之来旁敲侧击陈独秀”。于是瞿秋白以“身体不适,需要休养”,向中央请假,悄悄上了庐山,开始撰写“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
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此前瞿秋白撰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已在党的代表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中广为散发,五大开幕式的会场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这本7万余字的小册子。这本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什维克主义》的小册子,洋洋洒洒点名罗列了彭述之的17条错误。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坚持右倾错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组织活动,同年11月被党中央开除党籍。彭述之和陈独秀围绕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两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后由分歧转为完全对立,最终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