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十五日,福王朱常洵正式搬入其建于封地洛阳的王府,这意味着朝臣们在国本之争中的大胜利,皇太子朱常洛最大的竞争对手终于离开了。
万历帝被迫让爱子离京,心中自是千万不舍,因此赏赐福王钱财无算,王府规模也远超常制,引来一时非议。
对于福王就国之事,同样有着锥心之痛的,还有洛阳一带的各级官吏。明朝地方上的诸位藩王,一向多以贪婪淫乱出名。福王一家赴洛阳府邸,无疑意味着,一片硕大的乌云即将飘来。
这一切,都被一个名叫文翔凤的人看在眼里。就在福王离京前夕的万历四十一年,文翔凤从山东莱阳调任到河南伊阳(今汝阳),两年后又任洛阳知县。
可以说,这位文知县在伊、洛任职之时,恰好是福王府开创前后。而他又是一位醉心于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这数年间的施政纲要与大事,均被文翔凤记录在他的作品《孔迩录》中。
到底福王就国,给伊洛地区带来了怎样的骚乱?而万历末年,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底层社会还有哪些暗潮涌动?
让我们跟随文知县留下的回忆录,管中窥豹一番。 拿简单的施刑来说,文翔凤会根据罪犯身份的不同,分别用大中小三种不同尺寸的木板行刑。
老百姓犯法专用的板子是其中最小号的;另外他还有个习惯,无论堂下之人犯了多重的罪,一天绝不打罪犯超过20板。
即便上司特命要用重刑,文翔凤也一定会分成几天打完。
拿简单的施刑来说,文翔凤会根据罪犯身份的不同,分别用大中小三种不同尺寸的木板行刑。
老百姓犯法专用的板子是其中最小号的;另外他还有个习惯,无论堂下之人犯了多重的罪,一天绝不打罪犯超过20板。
即便上司特命要用重刑,文翔凤也一定会分成几天打完。
 文翔凤看到衙门里要造一批新枷把旧的换下来,便授意“其枷杻孔眼务要宽阔”,把木枷的孔造大一圈,这样能让受刑的人舒服一些。新造木枷还特地使用了旧枷的木料作枷心,原因是文凤翔害怕“新枷木气伤人”。
此外,文还嘱咐衙官不得擅用夹棍和桚指,“重事不过十板,轻事不过五板,夹棍私入衙者,重究狱卒。”
然而,就是这么个宅心仁厚的文翔凤所在的伊阳县,却是一个充斥着“罪大恶极”凶徒们的地方。
礼教向来是古代社会的稳固基础,文翔凤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上任后便强调要手下旌表贞洁女子,以正风气。
你能想象文翔凤听见“从来”二字后心里有多少匹羊驼奔过吗?
表彰贞洁烈女,今人往往于潜意识里,就把它与禁锢女性婚姻自由、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联系起来,抨击其为封建社会的一大流毒。
思维原始的地区直到现在还将婚配权当作一种商品,死了丈夫的媳妇,对婆家来说,也是一件商品啊。
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祥林嫂,守寡之后,因为婆婆贪财,逼迫她改嫁,实则是把媳妇卖了出去。
这并不是小说家凭空虚构的故事。真要说起来,严格受贞操观约束的,在明朝也不过是皇族女子,以及朝廷命官家的夫人而已。
贞节牌坊的存在,就站在了这种婚姻买卖现象的对立面,虽然还没做到能完全做到捍卫女性权利的地步,但是这也给那些丧偶的妇女一个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婆家强迫自己,还可以搬出这一套理论支持自己。至于那些旧情难舍,再不改嫁的守寡女子,旌表节烈甚至能起到保护她们性命的作用。
文翔凤看到衙门里要造一批新枷把旧的换下来,便授意“其枷杻孔眼务要宽阔”,把木枷的孔造大一圈,这样能让受刑的人舒服一些。新造木枷还特地使用了旧枷的木料作枷心,原因是文凤翔害怕“新枷木气伤人”。
此外,文还嘱咐衙官不得擅用夹棍和桚指,“重事不过十板,轻事不过五板,夹棍私入衙者,重究狱卒。”
然而,就是这么个宅心仁厚的文翔凤所在的伊阳县,却是一个充斥着“罪大恶极”凶徒们的地方。
礼教向来是古代社会的稳固基础,文翔凤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上任后便强调要手下旌表贞洁女子,以正风气。
你能想象文翔凤听见“从来”二字后心里有多少匹羊驼奔过吗?
表彰贞洁烈女,今人往往于潜意识里,就把它与禁锢女性婚姻自由、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联系起来,抨击其为封建社会的一大流毒。
思维原始的地区直到现在还将婚配权当作一种商品,死了丈夫的媳妇,对婆家来说,也是一件商品啊。
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祥林嫂,守寡之后,因为婆婆贪财,逼迫她改嫁,实则是把媳妇卖了出去。
这并不是小说家凭空虚构的故事。真要说起来,严格受贞操观约束的,在明朝也不过是皇族女子,以及朝廷命官家的夫人而已。
贞节牌坊的存在,就站在了这种婚姻买卖现象的对立面,虽然还没做到能完全做到捍卫女性权利的地步,但是这也给那些丧偶的妇女一个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婆家强迫自己,还可以搬出这一套理论支持自己。至于那些旧情难舍,再不改嫁的守寡女子,旌表节烈甚至能起到保护她们性命的作用。
 在文翔凤到任伊阳没多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惨案:伊阳寡妇王氏,从丈夫曹自新去世后便独自含辛茹苦抚养5岁的儿子,“居节十八年,茹尽艰辛”。
但不知是为了家财,还是日常生活中就有矛盾,王氏的公公曹文邦的小妾仝氏,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居然使得曹文邦将这个为家庭付出青春的儿媳扫地出门。
可怜的王寡妇,在仝氏的“百计折挫”之下,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
听说这桩惨案后,文翔凤“忍泪酸心”,下令将嚼舌头的小妾仝氏抓来,处桚指250次的重刑,“以偿其恨”,并为王氏厚葬,“题节妇之旌,以慰逝者”。
文翔凤还无比痛心的写道:之前我亲自交待属下们寻找节妇,结果大家都说境内没有人达到旌表的标准,那王氏又是什么人呢?
全都怪我疏于查察,这才使得贞洁烈女含冤而死。以后但凡有守节三年以上的人,全部报告给官府知晓,赐给她们粮食布匹。
如果害怕被强逼改嫁,可以由朝廷给予官方凭证,保障她们守节的自由。
如果能早一点有文凤翔这样负责的知县到来,如果早一点停摆的旌表工作能恢复,王氏有了朝廷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法律上的保护,何至于遭受到家族内部的迫害,自尽身死?
在文知县先前三令五申的督促之下,伊阳的官吏们终于找到了两名满足条件的节妇。
伊阳县虽然不大,但也不小,更兼此前多年未有旌表。现在全县只找出两人,未免太少了点。
难道是当地媒婆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平民家丧夫女子都能找到对象?
在大明律中,对利用巫术煽动并聚集民众的行为,有严厉的打击条款: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相比伊阳这里发生的一切,大明律里写的还是图样。
文翔凤在此所见到的场景,是城内外白莲教等邪教肆虐,地方妖人“嗜利嗜淫”,自称活佛,“妄称闻见鬼神”,以此诳骗无知良民。
在文翔凤到任伊阳没多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惨案:伊阳寡妇王氏,从丈夫曹自新去世后便独自含辛茹苦抚养5岁的儿子,“居节十八年,茹尽艰辛”。
但不知是为了家财,还是日常生活中就有矛盾,王氏的公公曹文邦的小妾仝氏,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居然使得曹文邦将这个为家庭付出青春的儿媳扫地出门。
可怜的王寡妇,在仝氏的“百计折挫”之下,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
听说这桩惨案后,文翔凤“忍泪酸心”,下令将嚼舌头的小妾仝氏抓来,处桚指250次的重刑,“以偿其恨”,并为王氏厚葬,“题节妇之旌,以慰逝者”。
文翔凤还无比痛心的写道:之前我亲自交待属下们寻找节妇,结果大家都说境内没有人达到旌表的标准,那王氏又是什么人呢?
全都怪我疏于查察,这才使得贞洁烈女含冤而死。以后但凡有守节三年以上的人,全部报告给官府知晓,赐给她们粮食布匹。
如果害怕被强逼改嫁,可以由朝廷给予官方凭证,保障她们守节的自由。
如果能早一点有文凤翔这样负责的知县到来,如果早一点停摆的旌表工作能恢复,王氏有了朝廷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法律上的保护,何至于遭受到家族内部的迫害,自尽身死?
在文知县先前三令五申的督促之下,伊阳的官吏们终于找到了两名满足条件的节妇。
伊阳县虽然不大,但也不小,更兼此前多年未有旌表。现在全县只找出两人,未免太少了点。
难道是当地媒婆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平民家丧夫女子都能找到对象?
在大明律中,对利用巫术煽动并聚集民众的行为,有严厉的打击条款: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相比伊阳这里发生的一切,大明律里写的还是图样。
文翔凤在此所见到的场景,是城内外白莲教等邪教肆虐,地方妖人“嗜利嗜淫”,自称活佛,“妄称闻见鬼神”,以此诳骗无知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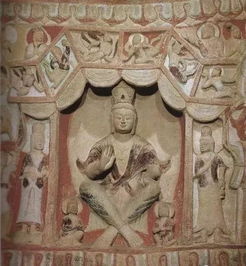 在这群邪教徒的刻意诱导下,伊阳村社中乃至出现“遂使男女,促膝淫秽”之场面。
假借鬼神之名搞起了堪比“海天盛筵”的活动,且“四境成风,牢不可破”,尤以城北情况最为严重。
在邪术蛊惑之下,伊阳的妇女与巫师及其信徒们过着“多姿多彩”的性生活,称其为滥交都不为过。
如此一来,你还能指望当地能剩下几个“贞洁烈女”能给朝廷旌表呢?
这等败坏风气之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文翔凤对此亦是痛心疾首:
“邵程大贤之乡,流风余韵尚在士林,村社蚩氓,无礼无法,不知有廉耻畏惮。本县长尔等,安忍坐视其乱,置之不问?夫骗财特其小小,尔辈亦人也,妇女以人为尽夫,中间岂无有头面晓事体者,曾不痛恨于心乎?况民间相聚,动成数十百人,此作乱之渐。”
“人尽可夫”一词都出来了,大家伙已经能猜到伊阳底层百姓受邪术荼毒之深,所谓“禽门丑状,不忍缕举”。
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万历后期,白莲教发展到了新高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礼部上奏称白莲教已是“天下处处盛行”,再不禁止恐怕会“有张角、韩山童等之祸”。
从文翔凤的记录,可知《明实录》中描写的情况绝非夸张之辞。崩坏前夜的人心骚动,已经借着宗教遍布国家的各个角落。
“本县不令而执之,非父母之体,特遍谕前项人等,速行解散,各收管其妇女,毋得仍前烧香作会。保正人等,仍朔望具结到县,如不奉律令,不遵禁约,定执其渠魁,以律从事。各乡约保正,说与廉耻法度!”
要是早先时候,这种情况抓一两个典型,重判游街以告众人尚可勒马,但文知县来的时候已经凉了,这哪是县城,整个一欲望之都。
见微知著,万历时的明朝这种现象早已“遍地开花”,朝中不作为,皇帝也不闻不问,上行下效,再假以时日发酵,而由此产生的,便是晚明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
《明史》中将明朝灭亡之祸起归结到万历怠政上,所谓“实亡于神宗”。
不过,明清之际的地方志,还有小说传奇之中,却充满着对万历朝治世的怀念。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明万历间,五谷丰登,六畜繁盛,至天启、崇祯间,生齿渐庶,俗尚渐奢,亨极而剥,已兆兵荒之祸矣!崇祯四年,流寇破城,焚掠殆尽。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几尽。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鳞,米价腾贵,税粮四岁并征,民大困。十三年,岁大祲,米价数倍平时,民多饿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仅存孑遗!”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起数百年前,北宋灭亡的前夜,不也正是宋徽宗“丰亨豫大”的物质大丰富时期吗?
苏州的著名景点虎丘,其断梁殿旁的这块石碑,是明隆庆二年(1568)所立有关禁止“荡子携妓携童”者及“妇女冶容艳妆”者游虎丘的官方法规。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为了照顾“览胜寻幽”的士大夫们的心情。碑文中还称,如果发现妇人在虎丘游玩,向官府举报核实之后,该妇人所带财物就会被当做奖赏赐予举报者。
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官府出面,也阻止不了士大夫眼中的俗人们附庸风雅的心。
虎丘依旧游人如织,文人墨客们也只好满怀怨念的感慨如此风景竟不免化为庸俗之所: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
然而,不可回避的却是,从万历皇帝驾崩,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只隔不到十年而已。
变数,的确是从万历朝最后一段日子开始了。《沁水县志》中所写的“亨极而剥”,实在恰如其分。
在这群邪教徒的刻意诱导下,伊阳村社中乃至出现“遂使男女,促膝淫秽”之场面。
假借鬼神之名搞起了堪比“海天盛筵”的活动,且“四境成风,牢不可破”,尤以城北情况最为严重。
在邪术蛊惑之下,伊阳的妇女与巫师及其信徒们过着“多姿多彩”的性生活,称其为滥交都不为过。
如此一来,你还能指望当地能剩下几个“贞洁烈女”能给朝廷旌表呢?
这等败坏风气之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文翔凤对此亦是痛心疾首:
“邵程大贤之乡,流风余韵尚在士林,村社蚩氓,无礼无法,不知有廉耻畏惮。本县长尔等,安忍坐视其乱,置之不问?夫骗财特其小小,尔辈亦人也,妇女以人为尽夫,中间岂无有头面晓事体者,曾不痛恨于心乎?况民间相聚,动成数十百人,此作乱之渐。”
“人尽可夫”一词都出来了,大家伙已经能猜到伊阳底层百姓受邪术荼毒之深,所谓“禽门丑状,不忍缕举”。
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万历后期,白莲教发展到了新高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礼部上奏称白莲教已是“天下处处盛行”,再不禁止恐怕会“有张角、韩山童等之祸”。
从文翔凤的记录,可知《明实录》中描写的情况绝非夸张之辞。崩坏前夜的人心骚动,已经借着宗教遍布国家的各个角落。
“本县不令而执之,非父母之体,特遍谕前项人等,速行解散,各收管其妇女,毋得仍前烧香作会。保正人等,仍朔望具结到县,如不奉律令,不遵禁约,定执其渠魁,以律从事。各乡约保正,说与廉耻法度!”
要是早先时候,这种情况抓一两个典型,重判游街以告众人尚可勒马,但文知县来的时候已经凉了,这哪是县城,整个一欲望之都。
见微知著,万历时的明朝这种现象早已“遍地开花”,朝中不作为,皇帝也不闻不问,上行下效,再假以时日发酵,而由此产生的,便是晚明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
《明史》中将明朝灭亡之祸起归结到万历怠政上,所谓“实亡于神宗”。
不过,明清之际的地方志,还有小说传奇之中,却充满着对万历朝治世的怀念。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明万历间,五谷丰登,六畜繁盛,至天启、崇祯间,生齿渐庶,俗尚渐奢,亨极而剥,已兆兵荒之祸矣!崇祯四年,流寇破城,焚掠殆尽。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几尽。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鳞,米价腾贵,税粮四岁并征,民大困。十三年,岁大祲,米价数倍平时,民多饿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仅存孑遗!”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起数百年前,北宋灭亡的前夜,不也正是宋徽宗“丰亨豫大”的物质大丰富时期吗?
苏州的著名景点虎丘,其断梁殿旁的这块石碑,是明隆庆二年(1568)所立有关禁止“荡子携妓携童”者及“妇女冶容艳妆”者游虎丘的官方法规。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为了照顾“览胜寻幽”的士大夫们的心情。碑文中还称,如果发现妇人在虎丘游玩,向官府举报核实之后,该妇人所带财物就会被当做奖赏赐予举报者。
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官府出面,也阻止不了士大夫眼中的俗人们附庸风雅的心。
虎丘依旧游人如织,文人墨客们也只好满怀怨念的感慨如此风景竟不免化为庸俗之所: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
然而,不可回避的却是,从万历皇帝驾崩,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只隔不到十年而已。
变数,的确是从万历朝最后一段日子开始了。《沁水县志》中所写的“亨极而剥”,实在恰如其分。
 今年年初,我在京郊一带访古,曾在涞水西岗塔旁找到一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当地人刻的石碑,详细描述了前一年北直隶旱灾的惨况:
“万历乙卯,亢旱异常,六月不雨…强壮者饥死于道路,幼弱者弃置于市井,卖子者充满于途,啼饥泣乞者遍野…”
其实,这场旱灾的范围并不止北直隶,山东也未能逃过这场灾祸:
“万历四十三年,山东春夏大旱, 千里如焚, 七月复蝗。”
就在北方这次大旱的同时,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在他的住地赫图阿拉城正式称汗,建国号金,年号天命。异日移国之渐,由此而始。
在华北大旱的前不久,中原已经出现了灾情。文翔凤在伊阳任职时,留下了有关他带领官吏百姓求雨的记录。
面对旱灾,在科学并不昌明的古代,父母官只能通过各种仪式向上天诉说自己的请求,祈祷神灵保佑。这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不过就是斋戒和诵经。
“本县恫念灵雨之不时,民将无麦无谷无花,斋沐步祷,阖宅蔬食,为民请命。而查出范应科、李追舟、王禄、冀思春等,违示屠沽,良心尽死!已行枷示。其买酒肉,以供饮喙,是诚何心?仰视苍苍,宁无肺腑!”
文翔凤不仅自己带头斋戒,还严惩了那些买酒肉享乐的属下,罚他们带枷示众。在文翔凤眼中,这群人已经没心没肺到拿全县百姓的生死当作儿戏的地步,如此严惩自不为过。
除此以外,文翔凤还不时亲自访查各个佛寺,防止僧人偷懒坐着诵经对神灵不敬:
“僧道坐而诵经大不敬。四门乡约,每日轮一门,在庙查看。除经案立诵外,仍僧道各轮六班,每时各一人,跪诵每卷毕,乡约同僧道童子拜礼,俱毋坐。本县仍不时查访。”
(所谓的乡约也就是农村自治组织,在嘉靖以后盛行于全国,具有官方认可的合法性,带有教化、救济、调解纠纷等职能)
虽然这么努力的敬神祈祷,但旱灾并没有怎么缓解:“雨不霈泽”。
有一次外出,文翔凤见到窑户们“尚作陶坏不辍”,便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烟出于地牖,本县向曾面戒而竟不悛,烈焰燎于坛侧,而欲甘澍惠于南亩,阴阳之气何由而通?即时泼灭烟火。至于城南地脉关本县王气不细,而窟陷日深,后将何极?汝水一北,谁杜鱼鳖?仍限五日内,各窑用隍中之土填平,灰滓运远方,隍池亦毋许深陷。其窑尽改于西岭外……“
文翔凤觉得,大旱之时还烧造陶瓷,烟火都从地下涌上来,就这还指望下雨呢?便急忙下令把这些窑场都迁走。
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文翔凤这些做法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但你又能指摘他什么?在那么个认知条件下,文知县是那么的卖力,又是那么地无力。
在天灾面前,人力是多么的渺小。反复无常的气候,已经开始为这个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
皇帝长期怠政,官职缺员也越来越多,本身帝国的运转已经出现了问题。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出现了北方天灾之后,“盗贼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诏令不行”的境况。
现在,撕毁万历朝的太平面纱,只在刹那之间了。朝廷无力也无心进行切实有效的赈灾,百姓在生死线上来回挣扎,最后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今年年初,我在京郊一带访古,曾在涞水西岗塔旁找到一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当地人刻的石碑,详细描述了前一年北直隶旱灾的惨况:
“万历乙卯,亢旱异常,六月不雨…强壮者饥死于道路,幼弱者弃置于市井,卖子者充满于途,啼饥泣乞者遍野…”
其实,这场旱灾的范围并不止北直隶,山东也未能逃过这场灾祸:
“万历四十三年,山东春夏大旱, 千里如焚, 七月复蝗。”
就在北方这次大旱的同时,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在他的住地赫图阿拉城正式称汗,建国号金,年号天命。异日移国之渐,由此而始。
在华北大旱的前不久,中原已经出现了灾情。文翔凤在伊阳任职时,留下了有关他带领官吏百姓求雨的记录。
面对旱灾,在科学并不昌明的古代,父母官只能通过各种仪式向上天诉说自己的请求,祈祷神灵保佑。这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不过就是斋戒和诵经。
“本县恫念灵雨之不时,民将无麦无谷无花,斋沐步祷,阖宅蔬食,为民请命。而查出范应科、李追舟、王禄、冀思春等,违示屠沽,良心尽死!已行枷示。其买酒肉,以供饮喙,是诚何心?仰视苍苍,宁无肺腑!”
文翔凤不仅自己带头斋戒,还严惩了那些买酒肉享乐的属下,罚他们带枷示众。在文翔凤眼中,这群人已经没心没肺到拿全县百姓的生死当作儿戏的地步,如此严惩自不为过。
除此以外,文翔凤还不时亲自访查各个佛寺,防止僧人偷懒坐着诵经对神灵不敬:
“僧道坐而诵经大不敬。四门乡约,每日轮一门,在庙查看。除经案立诵外,仍僧道各轮六班,每时各一人,跪诵每卷毕,乡约同僧道童子拜礼,俱毋坐。本县仍不时查访。”
(所谓的乡约也就是农村自治组织,在嘉靖以后盛行于全国,具有官方认可的合法性,带有教化、救济、调解纠纷等职能)
虽然这么努力的敬神祈祷,但旱灾并没有怎么缓解:“雨不霈泽”。
有一次外出,文翔凤见到窑户们“尚作陶坏不辍”,便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烟出于地牖,本县向曾面戒而竟不悛,烈焰燎于坛侧,而欲甘澍惠于南亩,阴阳之气何由而通?即时泼灭烟火。至于城南地脉关本县王气不细,而窟陷日深,后将何极?汝水一北,谁杜鱼鳖?仍限五日内,各窑用隍中之土填平,灰滓运远方,隍池亦毋许深陷。其窑尽改于西岭外……“
文翔凤觉得,大旱之时还烧造陶瓷,烟火都从地下涌上来,就这还指望下雨呢?便急忙下令把这些窑场都迁走。
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文翔凤这些做法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但你又能指摘他什么?在那么个认知条件下,文知县是那么的卖力,又是那么地无力。
在天灾面前,人力是多么的渺小。反复无常的气候,已经开始为这个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
皇帝长期怠政,官职缺员也越来越多,本身帝国的运转已经出现了问题。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出现了北方天灾之后,“盗贼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诏令不行”的境况。
现在,撕毁万历朝的太平面纱,只在刹那之间了。朝廷无力也无心进行切实有效的赈灾,百姓在生死线上来回挣扎,最后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编修的《伊阳县志》中如此哀叹:
“伊在有明时颇称殷庶,因流寇变起,焚掠殆尽。国朝定鼎以来,邑令加意招徕,虽惊鸿稍集,半非土著,殆不及百之一矣。所列诸镇亦止略似村落,而懋迁寥寥,难语集市。”
离崇祯自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伊阳的地方官虽然尽力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却始终不复过往繁荣景象。县里下辖的各市镇,只相当于明朝时候一个村落的规模罢了。
在伊阳任职两年之后,1615年,也就是华北大旱的这一年,文翔凤调任到洛阳为知县。临行之前,文翔凤向伊阳的父老乡亲深情告白:
“本县之食于伊者两载且四阅月矣,一滴一粒皆尔血膏…光阴迅使,初志空勤,本县遂别尔曹矣。身虽在洛,而心常在伊。可为父老效一臂者,不敢以我躬不阅,而遂置去。父老子弟,尚亦黾勉善行,共享天和,毋怠。”
伊阳百姓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告别了文翔凤后,就再也等不到那个”共享天和”的未来了。
当年五月末,发生“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紧接着便是畿辅大旱。
四月十四日夜,随着福王就藩的护卫军七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挑拨下,“齐至东门,挟赏鼓噪,震动地方”。
兵变的原因,按后来河南巡按张至发的奏折,极有可能是本该下发的赏钱没有到位:
“乞严谕福府辅导官,一切赏赍俱预先启王,依时颁给,毋得推诿恡啬,以招怨讟,致损威重。”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编修的《伊阳县志》中如此哀叹:
“伊在有明时颇称殷庶,因流寇变起,焚掠殆尽。国朝定鼎以来,邑令加意招徕,虽惊鸿稍集,半非土著,殆不及百之一矣。所列诸镇亦止略似村落,而懋迁寥寥,难语集市。”
离崇祯自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伊阳的地方官虽然尽力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却始终不复过往繁荣景象。县里下辖的各市镇,只相当于明朝时候一个村落的规模罢了。
在伊阳任职两年之后,1615年,也就是华北大旱的这一年,文翔凤调任到洛阳为知县。临行之前,文翔凤向伊阳的父老乡亲深情告白:
“本县之食于伊者两载且四阅月矣,一滴一粒皆尔血膏…光阴迅使,初志空勤,本县遂别尔曹矣。身虽在洛,而心常在伊。可为父老效一臂者,不敢以我躬不阅,而遂置去。父老子弟,尚亦黾勉善行,共享天和,毋怠。”
伊阳百姓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告别了文翔凤后,就再也等不到那个”共享天和”的未来了。
当年五月末,发生“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紧接着便是畿辅大旱。
四月十四日夜,随着福王就藩的护卫军七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挑拨下,“齐至东门,挟赏鼓噪,震动地方”。
兵变的原因,按后来河南巡按张至发的奏折,极有可能是本该下发的赏钱没有到位:
“乞严谕福府辅导官,一切赏赍俱预先启王,依时颁给,毋得推诿恡啬,以招怨讟,致损威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迩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文翔凤在伊洛施政的方方面面,财政、民生、移风易俗,各有千秋。
而其中有一类政务很是特别,都围绕着新立的福王府展开。
史书中说福王朱常洵就国之时,万历帝尽出宫中奇珍异宝赏赐爱子,又赐庄田两万顷、淮盐盐引三千张,连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都被一并给了福王。
可是,这样的说法毕竟太过笼统,福王到底在封地过着多奢侈的生活,光看土地和盐引这些词我可想象不出来。
幸运的是,《孔迩录》就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福王府的器用陈设及日常消耗。为什么文翔凤一个知县要记录这些东西呢?
很简单,供给王府的物资是需要洛阳附近州县分摊办理的,属于公务。另外我们也说了,文翔凤是个好人,抑制王府的为非作歹尽量为百姓谋福利,也是他施政的重心。
比如在《请免办福府龙碗》中,文翔凤表示福王所用的碗碟,需要“求之豫章”,到江西购买,“长途资乏”的同时,“木漆之工,数繁期迫”,所以他希望上峰能“酌赐量免”,减少一些地方的财政压力。
《孔迩录》内的《报府第棚殿安设》篇中,文知县从米豆草料,到鸡鸭鱼肉算起,知无不言:
“查得本县于役王事者三。其一则府第安设,其二则棚殿安设,其三则续造府第。
其为府第之安设者,为龙凤绒毡,为三号红毡,为八仙桌,为漆桌,为灯挂椅,为综床,为六角纱灯,为祭帛匣,为浴桶,为浴盆,为巨席,为蒸笼,为红布袋,为红麻酒络,为石磨盘,为铁锅,以件计者概一千二百五十。
为苏木,为锡,为荆条,为柴,为炭,为煤,为盐,为鱼肉,为椒,为蜜,为蒜,为大料,为红蜡烛,为粉,为生姜,为香油,为桦皮,以斤计者概八万五千六百四十。
为稻米,为粟米,为麦,为面,为绿豆,为黑豆,为黍,为莞豆,为枣,为胡桃,为柿饼,为胶枣,以石计者概三百八十。
为豚,为羊,为鸡,为鹅,为鸭,为兔,以只计者概六百三十。
按锦帐之属,原有府第之议裁剪者,委官办自苏州,以三千金计。
其为棚殿之安设者,则为回青龙瓯,回青龙碗,为回青龙冰盘,为细瓷瓯碟,概四千有二百。
为龙方桌,为龙头衣架,为大门屏,为梳背床,为一封书床,为油桌,为灯挂椅,为红扛架,为高角纱灯,为造膳红纱桌,为更鼓架,为马槽,为水桶,为金手盒,为金茶盘,概三百九十有八。
为荆芭,为铜铁锁,为铁麻搭,为铁火钩,为木梆,为铁铃,概五百有三十。
马黍十石,马草千斤,此皆刻期办之,而龙瓯则求之襄阳,其脚力,郡曾议之否邪?
其为续造府第之安设者,则铜火盆一,编铜为罩,以十五金取之汴上者,而小床又十,锅又九十,并葢为帐幔者又九。”
锦帐是花了三千两银子从苏州买来的,龙瓯则取自襄阳,铜火盆来自汴上,再加上之前江西的陶瓷碗碟。
除了直接为福王府办理各项生活物资之外,洛阳还要为福王提供车马船只人力,将这位大王的妃妾家人和财产仪仗从京城运到王府。
照就例,藩王就国所用船只不过500艘。可福王赴洛,便一次征调船只达1200有余。
1604年,福王大婚时花费40余万两,是叔叔潞王婚礼费用的4倍有余,几乎和给李太后加两次徽号的支出总和相当。
“王船行李自运河入黄河,至孟津登岸,以夫役运抵洛阳…王之仪仗扈从自卫辉登岸,直抵洛阳。议者谓两运之来速,于是集各县之夫于河干,伊川即小,亦至二百名。以尉部之,日费十金。运船之不至,夫不敢告归,迨三运至而两运尚杳然,故其无益之费殊甚。”
洛阳附近州县聚集了无数民工在运河边,准备帮福王搬行李。
结果王府的船队走的拖拖拉拉的,河南又不敢让工人们回去,只能花钱留住工人们一天天等着,造成了巨大的行政浪费。
而福王那多达两万顷的田地,不可能由他亲自照管,便委托王府太监们日常巡视丈量。这群宵小之辈,仗着王命,又怎能不趁机作威作福骚扰地方?
“礼遇之不至,恐其诬田以为硗芜,或鞭其承佃之地主。小民素不经中使之蹂躏,闻风而色为变矣。况可使之长为王民乎?”
这些属于福王的庄田,能给它们的主人带来多少收入呢?
“夫亩之以三分输也,顷之以二万计也,当收输金六万,日二百金,中民二十家之产,不足当一日…”
一年六万两,差不多等于每天两百两。二十户中等人家的收入,比不上福王府一天田赋的盈利。
纵然富甲海内,福王实际上也只能乖乖呆在洛阳王府里。明朝有祖制,藩王除扫墓迎驾之外,不得出城。身为当今皇帝的爱子又如何,再大能大的过先皇吗?
《明史》中记载,福王“日闭阁饮醇酒”,不仅是事实,更是无奈。但他的这种无奈,是建立在竭尽百姓膏血的基础上的。
“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诡异无常的天灾,群聚而起的流民,终于将福王和整个失控的帝国一起推向了深渊。
出土的《大明福忠王圹志》中说朱常洵被杀前“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王府里“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也有人根据圹志的内容,认为明末史料记载的李自成将福王与鹿肉同煮,办了一场“福禄宴”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墓志这种东西,一向出了名的“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并不一定比史书准确多少。
比如福王在墓志中还得到了“居国敦厚和平,亲贤乐善”的评价,但根据文翔凤的《孔迩录》来看,朱常洵只不过是个骚扰地方无止境的敛财狂魔罢了。
至于福禄宴之事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许义军只是从福王身上割下部分血肉充作菜肴,那么留有尸身也是正常的。
《明神宗实录》中,最后一次提到福王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二十一日: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迩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文翔凤在伊洛施政的方方面面,财政、民生、移风易俗,各有千秋。
而其中有一类政务很是特别,都围绕着新立的福王府展开。
史书中说福王朱常洵就国之时,万历帝尽出宫中奇珍异宝赏赐爱子,又赐庄田两万顷、淮盐盐引三千张,连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都被一并给了福王。
可是,这样的说法毕竟太过笼统,福王到底在封地过着多奢侈的生活,光看土地和盐引这些词我可想象不出来。
幸运的是,《孔迩录》就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福王府的器用陈设及日常消耗。为什么文翔凤一个知县要记录这些东西呢?
很简单,供给王府的物资是需要洛阳附近州县分摊办理的,属于公务。另外我们也说了,文翔凤是个好人,抑制王府的为非作歹尽量为百姓谋福利,也是他施政的重心。
比如在《请免办福府龙碗》中,文翔凤表示福王所用的碗碟,需要“求之豫章”,到江西购买,“长途资乏”的同时,“木漆之工,数繁期迫”,所以他希望上峰能“酌赐量免”,减少一些地方的财政压力。
《孔迩录》内的《报府第棚殿安设》篇中,文知县从米豆草料,到鸡鸭鱼肉算起,知无不言:
“查得本县于役王事者三。其一则府第安设,其二则棚殿安设,其三则续造府第。
其为府第之安设者,为龙凤绒毡,为三号红毡,为八仙桌,为漆桌,为灯挂椅,为综床,为六角纱灯,为祭帛匣,为浴桶,为浴盆,为巨席,为蒸笼,为红布袋,为红麻酒络,为石磨盘,为铁锅,以件计者概一千二百五十。
为苏木,为锡,为荆条,为柴,为炭,为煤,为盐,为鱼肉,为椒,为蜜,为蒜,为大料,为红蜡烛,为粉,为生姜,为香油,为桦皮,以斤计者概八万五千六百四十。
为稻米,为粟米,为麦,为面,为绿豆,为黑豆,为黍,为莞豆,为枣,为胡桃,为柿饼,为胶枣,以石计者概三百八十。
为豚,为羊,为鸡,为鹅,为鸭,为兔,以只计者概六百三十。
按锦帐之属,原有府第之议裁剪者,委官办自苏州,以三千金计。
其为棚殿之安设者,则为回青龙瓯,回青龙碗,为回青龙冰盘,为细瓷瓯碟,概四千有二百。
为龙方桌,为龙头衣架,为大门屏,为梳背床,为一封书床,为油桌,为灯挂椅,为红扛架,为高角纱灯,为造膳红纱桌,为更鼓架,为马槽,为水桶,为金手盒,为金茶盘,概三百九十有八。
为荆芭,为铜铁锁,为铁麻搭,为铁火钩,为木梆,为铁铃,概五百有三十。
马黍十石,马草千斤,此皆刻期办之,而龙瓯则求之襄阳,其脚力,郡曾议之否邪?
其为续造府第之安设者,则铜火盆一,编铜为罩,以十五金取之汴上者,而小床又十,锅又九十,并葢为帐幔者又九。”
锦帐是花了三千两银子从苏州买来的,龙瓯则取自襄阳,铜火盆来自汴上,再加上之前江西的陶瓷碗碟。
除了直接为福王府办理各项生活物资之外,洛阳还要为福王提供车马船只人力,将这位大王的妃妾家人和财产仪仗从京城运到王府。
照就例,藩王就国所用船只不过500艘。可福王赴洛,便一次征调船只达1200有余。
1604年,福王大婚时花费40余万两,是叔叔潞王婚礼费用的4倍有余,几乎和给李太后加两次徽号的支出总和相当。
“王船行李自运河入黄河,至孟津登岸,以夫役运抵洛阳…王之仪仗扈从自卫辉登岸,直抵洛阳。议者谓两运之来速,于是集各县之夫于河干,伊川即小,亦至二百名。以尉部之,日费十金。运船之不至,夫不敢告归,迨三运至而两运尚杳然,故其无益之费殊甚。”
洛阳附近州县聚集了无数民工在运河边,准备帮福王搬行李。
结果王府的船队走的拖拖拉拉的,河南又不敢让工人们回去,只能花钱留住工人们一天天等着,造成了巨大的行政浪费。
而福王那多达两万顷的田地,不可能由他亲自照管,便委托王府太监们日常巡视丈量。这群宵小之辈,仗着王命,又怎能不趁机作威作福骚扰地方?
“礼遇之不至,恐其诬田以为硗芜,或鞭其承佃之地主。小民素不经中使之蹂躏,闻风而色为变矣。况可使之长为王民乎?”
这些属于福王的庄田,能给它们的主人带来多少收入呢?
“夫亩之以三分输也,顷之以二万计也,当收输金六万,日二百金,中民二十家之产,不足当一日…”
一年六万两,差不多等于每天两百两。二十户中等人家的收入,比不上福王府一天田赋的盈利。
纵然富甲海内,福王实际上也只能乖乖呆在洛阳王府里。明朝有祖制,藩王除扫墓迎驾之外,不得出城。身为当今皇帝的爱子又如何,再大能大的过先皇吗?
《明史》中记载,福王“日闭阁饮醇酒”,不仅是事实,更是无奈。但他的这种无奈,是建立在竭尽百姓膏血的基础上的。
“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诡异无常的天灾,群聚而起的流民,终于将福王和整个失控的帝国一起推向了深渊。
出土的《大明福忠王圹志》中说朱常洵被杀前“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王府里“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也有人根据圹志的内容,认为明末史料记载的李自成将福王与鹿肉同煮,办了一场“福禄宴”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墓志这种东西,一向出了名的“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并不一定比史书准确多少。
比如福王在墓志中还得到了“居国敦厚和平,亲贤乐善”的评价,但根据文翔凤的《孔迩录》来看,朱常洵只不过是个骚扰地方无止境的敛财狂魔罢了。
至于福禄宴之事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许义军只是从福王身上割下部分血肉充作菜肴,那么留有尸身也是正常的。
《明神宗实录》中,最后一次提到福王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二十一日:
About The Author

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