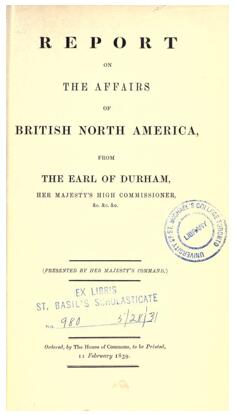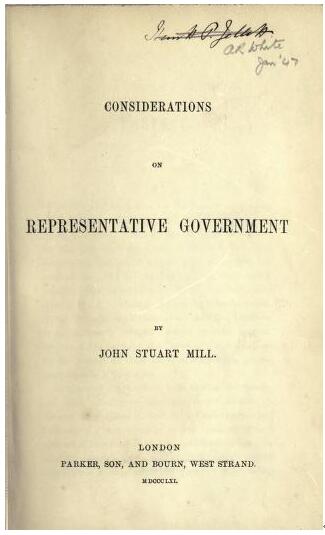英帝国:一个非正式帝国
作者:李旭
如果说美国革命之前的英帝国是一个自然的非正式帝国,那么之后很显然就是一个自觉的非正式帝国。图为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担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
一、国家的收缩化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族群关系在政治上的意义并不大。这是由于近代以前人类社会一般来说阶级分明、社会组织散漫,人们的阶级意识要比族群意识强得多。这样,族群很难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起作用,也就很难成为动员、压制或根除的对象。对很多人来说,统治就是统治,跟谁来统治、谁被统治关系不大:统治者不在乎统治对象是异族、本族,反正都是自家财产,不需要厚此薄彼;被统治者也不在乎,因为谁来也要纳皇粮。因此,异族君主称王为帝,在中外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由于这种政治冷漠的存在,对君王来说,统治异域他方其实难度并不大。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大众政治的演化,民主与民族主义联袂而来,族群开始慢慢变为实体单位,这就给统治几方土地的统治者们制造了新的治理难题。一方面,被统治者开始对政府提出了公共服务/福利方面的要求,这样在各族之间就出现了对政府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统治者自身需要寻找政治根基,伪装成民族之子是最为简便的做法。统治者再也不能扮演超然角色,必须选边站队 。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才在《民主的阴暗面》一书中指出,种族清洗这回事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现象。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国家的收缩化。 在近代之前,国家的形式与覆盖范围可以具有相当的弹性,各种人类社会的碎片几乎都可以随机地塞到一个国家的版图之内。但是现在,在组成一国的多元成分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契约”机制。而这些机制本身是受到条件限制的,因为维持族与族的关系要求更正式化的安排。比方说,在过去,我大清可以通过皇族与蒙古上层贵族之间进行联姻来维护满蒙联盟,今天的国家领袖按照同样的方式去娶贵胄之女,就恐怕一点改善民族关系的作用都不会有了。
帝国,是一项广土众民的事业,其执掌者就自然而然,更加能感到这种“收缩化”的压力。由于帝国的多元性较一般国家要更强,更少平衡,因此,观察近代诸帝国怎么应对这种压力,就更有意思,能让我们看到很多历史教训,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
二、一个非正式帝国的起步
我们先从英帝国讲起。
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人走向大海,开始创建自己的帝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英国在帝国之初所做出的思索与选择就颇为独特。
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诗人兼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和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都觉得需要避免重蹈罗马的覆辙。他们从帝国的扩展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光荣与利益,还有现实的危险,即英国从帝国中所获得的好处未必是英国人的好处。
他们担心,帝国的扩展将需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队伍去管理延伸的领土,而这会带来三个风险:一是征服的成本超过收益,二是这些爪牙发展出自己的独特利益,三是王权会因此得而加强,从而颠覆国内的政治平衡。在他们看来,正是过度扩张覆亡了罗马的共和体制。
为打破帝国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人认为,不列颠帝国必须是一个较松散的帝国。怎么松散法呢?其一,不要由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陆上征服;其二,新帝国必须是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的基石是海上贸易;其三,帝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某种合作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指挥与统治。
比方说,哈林顿提出,与其迫使被征服区域臣服,或者是与之结成邦联,帝国中心只要保持某种领导权就行。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约1640—约1698)指出,以贸易为基石的海洋扩张的成本远远比大陆征服来得要低。作家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1662—1723)则论证道,贸易的需求将保证国家的军事需要由海军(而不是陆军)来支持,而海军对国家的自由没有威胁。
英国的帝国之路在一开始确实是按照这个路数进行的。我们可以说, 从一开始,英国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帝国。我们随后还可以看到,这种非正式性延续在它的整个帝国生涯。
三、不列颠到底能不能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英国海外殖民是以公司或社团方式进行的(由国王发给许可证),至十八世纪,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北美洲和印度占据大块地方。有些是商贸据点,有些则成长为一个个殖民地。随着各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它们慢慢成长为一个个社会,尤其在北美更是如此。
慢慢地,有一些难于解答的问题出现了:“殖民地或自治领在帝国结构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属民还是帝国的共同组织者?帝国的中央机关在哪里?它的管辖权止于何处?当帝国边缘部分与中央发生冲突的时候,裁定者是谁?”说得再具体一点,北美人民要不要为整个帝国纳税?如果纳的话,程序是怎么样的?与之类似的问题是,不列颠议会与北美各殖民地议会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不列颠议会有没有权力对北美立法?北美各殖民地的总督(和其他高级官吏)由谁来任命,又对谁负责?
在过去,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可英国革命以来,议会制政体和人民主权已经成为共识。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里,也开设了若干地方议会(早在1641年的时候,英国国王在给殖民地总督的指令中就明确要求召集由“自治市民”组成的议会)。既然如此,殖民地与不列颠母国的关系就费思量了:同为人民,何能厚此薄彼?北美人民/议会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就应该有一个说法。
不过,自十七世纪初至美国革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疑问一直是仅仅在理论上才有意义。原因是这样的:英国对北美一直疏于管理,既没有征税(直接税),也没有设官、设兵、设卡。英国与北美之间的贸易欣欣向荣,且北美殖民地人民离国不久,既有很强的英国认同,也要仰赖英国的保护。
从道理上讲,双方的关系要讲清楚,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未婚同居”。对这件事,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其1774年的一次演讲中是这么说的:“从一开始,殖民地便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构的支配,至于它根据的原则,他们则从没有探问过;我们允许他们享有大量的地方特权,至于这些特权又如何与英国的立法权威相一致,我们也不加过问……在此期间,双方对这一重叠的立法机构,都不曾感觉到不便;是人不能觉察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导致了这一机构的形成,而这些,则正是人间一切政府的重要支柱。这两个立法机构,虽时常发现它在履行着同样的功能,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制度性的冲突。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半世纪里的英帝国称作一个“自然”的帝国。它宛如一颗老榕树,根系四处蔓延,生长出一棵棵分支,它到底是一片森林,还是一棵大树,还很难说。
问题出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之后,国家负债累累(一亿英镑以上)。英王乔治三世即位不久(他是1760年登基的),颇思有为,任用老臣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enville,1712—1770)整顿帝国秩序,其重中之重又在北美(当时北美人口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以上,占英帝国总人口的两成以上)。
格伦维尔力查走私,又在北美殖民地引入了新的税收——印花税(1765年),从而引起绝大争议。这笔税本身倒不重(估计约二十万镑,摊到每个北美人身上大约一个先令多一点,约占北美年人均收入的五百分之一),其目的也是为了支撑英国在北美边境的驻军费用。但是,这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宪法问题。
日后大陆会议的代表、主张对英和解的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 1732—1808)以“一介农夫”(A Farmer)的署名,写就系列文章《宾夕法尼亚农夫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于1767至1768年间出版。他写道:“有些人觉得英国征收的税额很轻,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这种想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税额的轻重, 而在于英国议会是否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力。
老实说, 不列颠能不能向北美殖民地征税是笔糊涂账。 这是因为, 无论是在不列颠一方,还是殖民地一方,都各有一套说法可以对现状提出有效挑战。
在不列颠议会一方,可以说殖民地本身即来自于王室的授权,其前身不过是企业法人团体。从历史上看,不列颠确实一直在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和调节(尽管程度甚微)的事实证明了不列颠议会的高级属性(殖民地否认不了此种事实的存在)。虽说北美殖民地在不列颠议会中没有正式代表,但是根据英国宪政传统,长期形成的习惯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一种“同意”,所以不列颠议会为殖民地立法并不违反立法需得到受法律管束者同意这个宪法原则。
在北美殖民地议会一方,可以反驳说,帝国事务与邦国事务要分开。再说殖民地议会和不列颠议会建立于同等的基础上,都是一方民意代表,也都是习惯生成(不列颠议会获得主权也不过是光荣革命之后的事情,与北美殖民地议会处于某一个时间段),那为什么不能得到同等待遇,在各自领域内互不干涉?况且在过去,大家都是各行各道的。
四、一个正式帝国的难产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候双方的政治争论,充满了“自由、宪政、权利、主权”这样的字眼,大家都义愤填膺得很,其实捅破这层窗户纸,说的就是一个问题,英帝国的国体尴尬,就像一个巨人穿着一个小女孩的衣服。当时其实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紧要。
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伯纳尔(Thomas Pownall,1722—1805)在其1764匿名出版的著作《殖民地管理》(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onies)一书中说道:“大不列颠不应再被视为仅仅是这个小岛的王国,连带着诸多作为附属品的省份、殖民地、定居点以及其他外来部分,而是应当作为一个庞大的海洋体系,包容我们在大西洋和美洲的全部属地,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帝国。”另一位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1712—1779)在1765年写信给不列颠政府高官,也说道:“依我之见,在美洲所发生的所有政治罪恶,都源于大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之间关系未定这个事实。”
问题是,看到归看到,怎么联合却基本上无解。这里并不是说不列颠的国王和重臣就想坐在北美人身上作威作福。困难出在客观条件上。
过去我们对美国革命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美国革命是由对苛捐杂税和暴政的反抗而来,这个说法基本上已经被史学界否定。另一种说法则比较隐蔽,说北美人闹独立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已经成长起来了,翅膀硬了所以要单干,这个说法当然也不是真的(详见鄙著《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在部分意义上倒是反过来的: 与其说是北美成长得太大,瓜熟蒂落要搞革命,倒不如说北美还成长得不够快、不够大,导致了不列颠作为一个正式帝国的难产。
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们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帝国联合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北美各殖民地向不列颠议会派出代表,当时有一大批人提出这个建议。用其中一人的原话来说,“(只有这样才能)给双方带来持久和切实的好处,或者我应该这么说,避免双方彻底毁掉自己”。
问题在于英国的议会体制是多数民主制。现代政治学通常认为,这种政治体系将政治权力集中到多数当选派手中,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和少数界限相对固定,那么这种政治体系与程序很容易造成多数合法的政治垄断。所以在一个分裂社会(divided society)中实行这种体制,有时非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会促进冲突的激化。在英美问题上即是如此,不列颠太大,北美太小,北美派出的代表没有办法在不列颠议会中形成平衡。
当然,如果仅仅是多数民主制的问题,政治上倒也有变通的办法。比方说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在1968年总结先人实践,提出了“协和民主”的想法,这种做法的主旨是让多数与少数共同分享政权。具体做法包括:
其一,政府组成人员里面包括所有主要政治板块的领导人,政治决策要以共识方式进行。其二,少数否决权,即为确保少数群体不被议会多数压倒,需要给予少数群体对其不喜欢的政策或立法以单方面的否决权。这意味着在特定的领域上采取极为苛刻的立法程序。其三,在政治的输入和输出部分,都要按照比例原则行事。其四,群体自治,让少数群体可以在专属地域或领域行使排他性权力。
但这套办法的问题在于应用的范围有限。大体而言,小国寡民,内部分化不要太多元,且各群体人口、实力不过分失衡是先决条件。像英国这种大帝国,就没法用了。
最后一招就是联邦制,但联邦制要行得通,一般认为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强而有力的行政机构,以对各邦的可能冲突进行调节。这点英帝国做不到,因为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北美,人们对王权都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国王很难违背任何一个立法机构的意愿,强行执行可能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政策。其二,各邦的实力最好大致相等,或差别不太大。这个条件也无法满足,因为整个帝国的国力分布太不平衡,不列颠独大。而且不列颠万难自降地位,将自己只看成是诸邦之一。
所以,如果北美殖民地更大、更强一点的话,英美双方倒是可能达成政治交易。但既然整个帝国中不列颠独大,美国弱小但又有潜力,双方就很难妥协了。
既然国家改革的方式走不通,那就只有诉诸武力一条路了。但是,不列颠又没有全心全意投入一场征服战争。英军在战争的早期,打的是以战促和的主意,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就没有抓住北美起义初期的脆弱时刻。到了后期,则是兵疲师老,国会又不肯掏腰包,也失去了国内民众的支持。于是只能认输了事。正式化帝国的努力就此失败。
五、一个自觉的非正式帝国的诞生
经此一役,不列颠的统治者知道厉害了。在之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再也没有人谈论建立帝国通盘管理体系这回事。
帝国税收计划被置诸脑后,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 1806;其中1783至1801、1804至1806年在任)指示:“应该避免出现类似以前发生的那样的误解,议会不再强行征收有关加拿大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税款的征收处置应该由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决定。”这种灰心丧气甚至到了“十年怕井绳”的地步,在要不要建设新的殖民地的问题上,美国革命之后的重要政治人物谢尔本勋爵(William Petty, 2nd Earl of Shelburne,1737—1805)甚至说道:“在经历了北美所发生的事情后,再来考虑殖民地似乎有些发疯。”
我把美国革命之后的英帝国政策称为“抓小放大”。“抓小”指的是英国对各殖民地的内部权力结构有所注重,抑议会而尊总督。“放大”则指的是英国从很多地方事务上大幅度后退,不再寻求从政治成熟的殖民地(标志就是有自己的议会)获得岁入,也不再寻求构建一个科层制的帝国 。
谢尔本勋爵在当时重提旧时代的论调:“我们的贸易先于统治。” 如果说美国革命之前的英帝国是一个自然的非正式帝国,那么之后,很显然它就是一个自觉的非正式帝国。
今日的研究者在谈论英帝国的非正式性的时候,主要是从1840年代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英国政治与外交时讲起的。亚当斯密(1723—1790)早在首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专门写过,传统的殖民地垄断贸易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而且会扭曲市场与生产。保留帝国实际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交易。稍后的许多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和约翰穆勒(1806—1873),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那就是“殖民地是帝国的负担”。这个倒不是以后“白人的负担”式的矫情,而确确实实是觉得英国从殖民地上无利可图。
后来两度担任首相的政治家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在1852年形容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典型想法。他们想的是,与其花大力气去征服、建设,不如保持某种势力范围、间接管制就好。但老实说,与其说是自由放任主义缔造了一个无形帝国,倒不如说是它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承认与发展:既然管制不易,不如少加管制 。
在这个时候,从表面上看,英国仍然是一个统一王国,大不列颠御策四方。但从现实上观察,维系这个帝国的,是无形的政治,而非有形的制度、官僚、军队与宪法。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其很多海外领地实际上是无法统治的(这主要指的是法理上的)。那么,如何统治不可统治之地,就是一门艺术。
|
|
历史上先后成为英帝国范围的地区。名称下标有红线的地名为今天的英国海外领土。
六、美国革命之后,英帝国何去何从
历来都有人称赞英国人“含混过关”的政治智慧,那就是暂且把法理争议放在一边,但凭常识做去,在实践中探索合理的政治边界;对已过时的旧制,不是骤然废除,而是不声不响,放在一边不去搭理,让新的实践慢慢覆盖之。
美国革命之后,英国对待其帝国,也正是如此。英帝国的国体与政体相互抵触,经美国革命一役,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英国人的帝国一开始就缺乏理性规划,但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事,已是既成事实。这样,大英帝国就有三条道可以选。
一是将错就错,整饬纪纲,但由于美国革命,英国人已经丧失了信心。二是任由某些殖民地独立,选择一个“小英格兰”。1849年以后,《航海条例》(这部法律让不列颠掌握了对帝国贸易与生产的垄断)被废除,重商主义方略被自由贸易政策所取代,就更没有经济理由来维系对帝国的掌控。最后一条路则是找到一种中间交际方式(也可以叫做“潜规则”),来调和结构上的矛盾。我称之为“无形政治”(相对于明显的制度行为而言)。从历史上看,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对第二种道路持相当同情态度,但实际选择的是第三条。
当然,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那个时代,英国的殖民地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和南非这样的白人移民占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另一类是英国在非洲、南美和亚洲的非移民型殖民地,如印度和牙买加等。在一般英国国民心中,前一类才是真正的帝国。上面所述的帝国矛盾也主要发生在第一类殖民地。
七、殖民地的自由与母国的主权:争议及实践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和日后的南非等诸殖民地(这些地方都是由若干小殖民地簇积而成,为行文方便起见,用日后的名称来称代它们),都涌现出了这样的问题:首先,本地的行政机关向谁负责?其次,本地的议会同英国议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地方立法同英国立法的关系如何?
我们按顺序谈谈这两个问题。首先, 本地行政机关是对本地议会负责呢,还是是英国政府的下级单位?如果答案是前者,就要建立所谓“责任制政府”,总督向地方议会负责。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总督就是英国政府的派遣官吏,地方议会只起襄赞作用。
在很多人看来,总督向谁负责是个主权问题。成立责任制政府会显然削弱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能力。1839年,殖民部大臣约翰· 罗素伯爵(John Russell,1792—1878)就说道:“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
美国革命发生之后,一部分英国官员觉得,革命之发生,原因就在于总督的权威太小,让本地议会恃宠而骄,所以加强总督权威,让本地议会“少一点自由”就是治本之法。1791年,英国提出《加拿大法案》(Constitutional Act 1791),根据该法案,总督的权威大大增强,他直接向英国主管殖民事务的部门负责,可以否决立法,可以解散议会,其薪俸也不受议会控制。在实际操作中,为了稳固总督的权威,总督任命一小群地方高层人士(终身任职)主持行政与立法参事会,主导殖民地事务,这是为了培养殖民地的亲英“贵族”阶层。这些人多半出身世家,是国教上层人士以及与英国有联系的大商人、地主,借总督权威把持地方,总督也要依赖他们才能顺利行政。
英国这么做,无非是想借人事政策来控制地方。增总督之权,以昭彰存在,与世家共治,以拉拢、分化地方。
老实说,英国的这套做法是典型的“好了疮疤忘了痛”。早在美国革命之前,英国治理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方式就是同本地的世家共治,这些人同伦敦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和商业往来。在帝国看来,这样一批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要仰赖帝国的恩惠,自然是帝国在北美大陆可靠的代理人。
问题是,这样一批人把持官职,就绝了中下阶层精英的进身之路。这自然就在殖民地的上层和中上层人士之间集聚起紧张关系。社会流动受阻,相当多的人就对北美的政治秩序(更深一层就是帝国的政治秩序)心怀不满。
美国革命的爆发,不能说与这种人事政策没有关系。在加拿大的实践,结果也很糟。上下加拿大的民众与总督并权势集团的关系都很糟糕,1837年11月到12月,在上下加拿大分别发生了民众武装暴动。这些暴动组织差、规模小,旋起旋灭,但是在英国震动很大。英国迅速任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德拉姆伯爵(Lord Durham,1792—1840)为加拿大总督。在调研之后,他提交了著名的《德拉姆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1839),z指出以前的做法不靠谱,应该在加拿大实现责任制政府。
|
|
《德拉姆报告》1839年版封面
他说道:“国王必须接受代议制度的必然后果。如果国王不得不继续使这个政府具有一个代议制机关,它就必须同意让获得代议制机关信任的那些人来继续管理政府……就殖民地而言,确保其完全的从属地位是靠殖民地能够在与帝国的继续不断的联系中获得好处。就母国政府而言,对殖民地涉及内部事务的法律的制定,或者对履行行政权力的人员的选择进行毫无根据的干涉,那么,这种从属关系肯定不能加强,只能大大削弱。”
英国的保守派对德拉姆的这个建议并不满意。托利党元老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1769—1852)宣称:“地方责任政府与大不列颠的主权完全是不一致、不协调的。”1843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Albert, Prince Consort,1819—1861)也说道:“我不认为英国王室会允许加拿大责任政府的建立 ,因为那将等于一个脱离母国的宣言”。
德拉姆等自由主义者则不认为殖民地组建自己的政府就会丧失对母国的附属关系,因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还存在着经济上、社会上的联系,保持对属国忠诚的办法不一定非要是制度上的。
这些自由派们的关键论点是,殖民地的自由与母国的主权并不截然对立,“自由要比屈从更能培育出忠诚”。日后四度担任首相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在1846年说道:“现在我承认,被任命的殖民地议会与行政机构并不是帝国权威的防护物,而是混乱、衰弱、分裂和不忠诚的源泉。”日后的加拿大总督、第八代额尔金勋爵詹姆斯· 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是这些自由派的一员,他也说道:“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你不能对殖民地说殖民地仅是一种临时的存在,你必须让殖民地相信,不隔断它们同大不列颠的联系,它们也可以达到成熟的程度。”
1846年自由党政府重新执政,恰好是德拉姆姻兄的格雷勋爵(Henry George Grey,1802—1894)成为殖民大臣,他写道:“在北美任何英属殖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格雷还评价道:“在尊重与否决加拿大人的意愿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否决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如果我们超越当地的立法机构,就必须用武力来维持我们的权威。”
格雷任命自己的女婿额尔金勋爵成为加拿大总督,实现了责任制政府。日后历经的沿革,大致说来是这么一回事:总督成为虚职,总督之外另设总理,成为实际的行政首脑,由议会选出又对议会负责。
在加拿大的这套政治实践迅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加拿大迅速安定下来。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 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1795—1861)后来被赦免,回到家乡时说,“如果我1837年时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看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
之后,在澳大利亚等地也相继实现了责任制政府。在这些地方,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澳大利亚政治家亨利· 帕克斯(Henry Parkes,1815—1896)在1847年羡慕地论及美国革命,到了1888年则宣称“(希望)这种最重要的亲缘关系将使我们与英国世世代代连接在一起。”
那么, 地方立法同英国立法的关系又如何呢?
《德拉姆报告》中还有另外一个建议,那就是帝国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分离。这指的是英国对有关殖民地事务的立法应该局限在政府体制、对外关系、贸易政策和公共土地管理几个领域中,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应该由地方自行处理。在以前,英国始终保留着对地方所有立法的干预权,而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既然英国已经承认了责任制政府原则,承认各殖民地议会对内部事务的统治权,那么顺理成章地就要立法厘清英国议会与各殖民地议会立法之间的关系。
到1865年,不列颠议会通过了《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该法的规定包括:
“只有用明确的语言和必要的解释表示该法能适用于殖民地的英帝国议会的法令,才能延伸适用于殖民地。……殖民地法不因违背了英国的制定法或与普通法相矛盾而失效;每个殖民地应有权创立法院,每个殖民地的代议制的立法机关,就其管辖权控制下的殖民地而言,应该享有并且被认为一直享有制定有关该立法机构之构成、权力和程序的法律的充分权力。”
简言之,这意味着,其一,各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不再从属于英国法,而只从属于帝国议会为各殖民地制订的特别立法;其二,各殖民地的内部宪政安排,自己决定即可(以加拿大1867年宪法为例,就是自己制订送到英国议会走一个程序通过)。这也意味着,英国议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地方议会的平等地位。
八、一个非正式帝国的尴尬:帝国联邦运动
责任制政府和地方立法有效性的明确这两件事确立了各殖民地(后来改称为“自治领”)在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地位。如果说这之前的大英帝国是一个自然的非正式帝国,从这一刻起则正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非正式帝国。
哲学家约翰· 穆勒(1806-1873)在1861年初版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是这么评价这种自觉的非正式状态的:
“大不列颠目前在理论上公然宣布并在实践上忠实遵守的政策的一项确定的原则是,它的属于欧洲种族的殖民地和母国同等地享有最充分的内部自治。……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否决权,尽管名义上保留,实际上仅仅对关系到帝国而不唯独关系到该殖民地的问题才行使(而且很少行使)。……每个殖民地因此对它本身的事务具有甚至作为最松散的联邦成员所能具有的充分权力,并且比在美国宪法下享有的权力充分得多,它们甚至可以自由地对从母国进口的商品随意抽税。它们同大不列颠的结合是最松散的一种联邦,但不是一种严格地平等的联邦,母国保留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实际上减少到极有限的程度。”
|
|
《代议制政府》1861年初版封面
这个评论很好的描述了这种非正式状态的性质:一方面各地方(自治领)拥有非常高的自治权,另一方面英国也保留了非常的统治权,垄断着帝国事务,但又严格限制使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英帝国确实是非同寻常的。既然各地都有责任制政府,各地方议会也有独立立法之能,既然并没有一个帝国总议会、总政府,也没有一部帝国宪法,那么认真讲起来,各地方在法理上为什么仍然从属于不列颠,就是一件很不好解释的事情。
这种不好解释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英帝国的尴尬状态。
一方面我们不能说相当多的殖民地人民没有英帝国认同,因为他们固然认为自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或南非人,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是英帝国公民。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把英国与英帝国分来看待,早在1774年,政治家埃德蒙· 柏克(1729—1797)就告诉自己的选民: “我们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成员,但这个国家本身又是一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日后的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1874—1965)也说了类似的话:“英国不能被视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它既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和联邦的创始者,也是他们的中心。”1915年,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也写道,普通的加拿大人把自己既看做加拿大人又看做英国人,因为帝国不是英格兰的帝国,英格兰充其量只是帝国内部众多民族中的一支。
但是在一方面, 英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确实难于安排英国与各自治领的合适地位。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讲述了英帝国如果要建设一个正式结构所会遇到的政治困难。这种政治困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稍轻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帝国联邦运动”的失败来描述这种困难。帝国联邦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在英国及自治领兴起的一种思潮与政治运动,目的在于统合帝国,为帝国提供一个正式的政治框架。当时世界正进入一个更激烈的经济竞争时代,英国人发现自己也非常需要整合自己的帝国,使它更有形化,以应对列强的挑战。英国历史学家P.J.马歇尔(P. J. Marshall,1933—)在《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中指出:“严肃的帝国主义者首先要关心的是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列颠民族再联合起来,而不是征服非洲的土地”,“在帝国主义者的各项纲领中,关键的问题是在英国及自治的各移民殖民地之间创建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
这个运动并不是由一小撮无名之辈及帝国主义狂热分子搞起来的,正相反,它在英国及各自治领的高层都受到相当的欢迎。当时的人们组织了一个“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这个协会诞生于1884年,解散于1893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等各地都有它的分支,英国首相罗兹伯利(Lord Rosebery,1847—1929)是这个协会的一员,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协会副主席。协会解散之后,还有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约瑟夫· 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在孜孜不倦地推动英帝国统合计划,张伯伦甚至为此赌上了自己成为英国首相的机会。
1887年,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在伦敦举行,旨在商讨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这在事先被视为“迈向更重大事情的第一步”。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1847 —1929)在开幕词中隐隐约约提到制宪方案。一位与会者评论道:“我们总可以亲眼见到这种非正式的帝国会议……发展为一个协商机构,也许有一日会成为……一个立法机构。”但是同这些人的殷切希望和良好的势头相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联邦运动最后还是无疾而终。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英帝国的正式化存在着结构上的困难。
帝国联邦主义者大体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方案。第一种是,组织一个帝国事务顾问委员会,让一批高阶人士出来为帝国事务出谋划策(但其决议没有约束力);第二种是,让各殖民地向英国议会派出代表,使英国议会能够代表帝国利益;第三种是,效仿美国,组织一个超越英国与各殖民地之上的联邦政府。
这些方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英国的政治文化。英国人总是对剧烈变革持谨慎与怀疑态度的,只要得过,总是且过为好。许多人认为,强求一个正式帝国只会带来“混乱、不幸和虚弱”。而现有的情况已经很好,“语言、文化、交流、历史、共通的习惯、体制和思考方式”足以保证帝国的统一,政治上的一统只是形式、外表与后果,不足为据。帝国联邦主义者是在强求一个“客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这么做只会将各地的利益冲突显性化,从而疏离而不是加强了帝国。
第二个困难就是上面这些方案实际上不适合“国情”。英国政治家会更偏向于扩容英国议会的方案,而各自治领的参与者更欣赏保留更多自治权的联邦方案。在非正式帝国中用模糊性维护起来的不列颠-自治领关系,非常难于用宪政语言表达出来。不列颠的事实优势地位与各自治领的特殊自治地位难于融合在一起。假如不列颠不是那么强,又或者说各自治领还没有发展出那么多自治特权,那么一个倾斜式的联邦体制也许能起到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目的。
正因为有这些困难,所以当时那些最有名的英国政治家,无论是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还是格莱斯顿,虽然多多少少有对帝国联邦计划抱有好感,但都没有为之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帝国联邦运动的失败,再次说明了组织一个正式帝国的困难。此帝国似乎非要采取非正式帝国的外形,才能维持。
那么,帝国是何以维系的?答案就是“无形政治”。
九、帝国的“有机团结”:无形政治
“无形政治”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词。英国人自己的说法是“有机团结”(organic unity),这是跟“机械团结”相对而言的,指的是国家的统一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物,就像一个活的生物一样。机械团结则指的是由法令、制度构成的一致。
有机团结这个词在帝国联邦运动的反对者那里常常能够听到,他们通常对宪法工程学不予置信,认为政治秩序一定是自然长成的。在我看来,有机团结这个说法颇有几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但“有机”这个概念仍然能很好的说明英国人的帝国思路。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没有确定无疑的宪法条文规定各方举止与权限的时候,政治秩序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的是参与者的默契、私下协调、对传统的尊重与自我克制。换句话说,英国的国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机”/“无形”的。我们发现,在第二英帝国(即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后的英帝国,之前的被称为“第一英帝国”)的绝大部分时期,这种眼光与手腕都同样也被应用到了帝国政治身上。
在十八世纪中晚期,埃德蒙· 柏克在其对美洲事务的演讲中就很清晰的表明了这种眼光与判断。他说道,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从理论上来说,必定无限,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力边界的。尊重这一自然形成的边界,有赖于主政者的克制与智慧。“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的脸上。”换句话说,贸然行使主权形式中的一部分,若与一地属民的利益冲突,会引起他们对于整个主权的质疑,这岂不得小失大?“这一权力(主权)不该纳入常制,也不能上来先用它。”换句话说,绝不能不顾具体的情势,一味的主张并行使抽象主权权利。
那该怎么维系属地与母国之间的关系呢?总结下来有这么几条:
首先,要避免母国和属地在主权原则上的争论,各自表述/笼统表述、不争论、装糊涂是不错的做法。其次是避免母国与属地之间发生争执,如果有争执也要极力避免上升到宪法层面,大事要化小。再次是着重协调。比方说,不列颠手上保留了六项权力:它可以制订或修改殖民地宪法,控制公共土地,调控帝国境内移民,调控贸易,主持司法上诉,主持外交政策。但除外交政策之外,行使其他权力的时候极为克制,一般都会预先同属地进行私下协调,在得到默认之后方才实施。再次是并不强求帝国内的政策、立法一致。正如前面穆勒所说,不列颠允许属地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控制关税(甚至是对母国课以歧视性的关税)。
一地主权谁属,从根本上来看有五个来源:武力、法理、利益、魅力、传统。法理指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利益指的是该地在该国内享受到的好处,魅力指的是母国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上的吸引力(或曰软实力),传统则指是该地管制的历史传承。所谓“无形政治”,就是英国人在武力、法理层面的缺失,用其他方面来弥补。虽然各殖民地与不列颠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当具体的争端由头被避免之后,这种“缺陷”就会被空置。通观英帝国的统治史,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治术有效降低了帝国内部的纷争。英国人发现,当统治不可统治之地时,有的时候帝国治理不是制度、技术,而是一种艺术。
如果从更学理/抽象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无形政治”其实是关系型契约对古典契约的替代。古典契约意味着所有的缔约条件在缔约时就得到明确、详细的界定,并且被界定的当事人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能准确度量。而关系型契约则意味着当事人更关心契约关系的持续,并且认识到契约的不完全性和日后调整的必要。有的时候,真的是“水至清则无鱼”。
从长远看,无形政治与有形政治相比各有优劣。无形政治的好处是较简易,维系帝国内部关系的成本会比较低。实践中,各自治领也确实培养出了对英国的忠诚之心。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十万加拿大、澳新、南非战士自愿为英国而战就是证据,还有什么比血税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忠诚心呢。事实上,如果以一战参战人数比率而言,澳大利亚人是要远远超过英国本土的(四百万人口中就有四十万以上参战)。
坏处是它只能维系而不能创制关系。在帝国本部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无形政治发挥的力量比较大。但是当帝国本部衰落之日,无形政治就力有不逮了。
十、结语
这正是英帝国在一、二战后的历史遭遇。
1917年,战时帝国会议承认了英国与各自治领同为帝国中的自治国家,这标志着以英国为主导的帝国走向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方向。一战后,英国彻底退出了对自治领事务的干预,其外交政策也实施了所谓“整个帝国普遍同意”原则(即帝国外交政策由各国联合控制),又逐渐从联合控制走向自主控制。
1926年,以枢密院议长及前首相阿瑟· 贝尔弗(Arthur Balfour,1848—1930)名字命名的《贝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of 1926)发布,澄清了各自治领的独立宪法地位。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规定了英国与自治领内政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这实际上宣告了英帝国的解体,以英联邦代替之。
以上多说的是坏处,但反过来想想, 如果没有无形政治在勉力维持,很可能英帝国也不会维系那么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可能就会弃之而去。在英帝国解体之后,英联邦仍然维持了相对的统一和融洽的关系,无形政治功不可没。
埃德蒙· 柏克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很清楚,阁下,自有粗鄙的政客群氓,堪称政治之机械工的,听完我这番话,会认为是不着边际,是狂想;……他们的眼里,除了粗鄙的、肉眼可见的货色,便再没有其他;这种人,绝没有资格做帝国之伟大航程的舵手,便是摇转这机器上的一个小轮子,他们也不配。”
本文所讲述的就是帝国治理中那些肉眼不可见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