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益观念的变迁
导读
现代慈善公益观念源自西方,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重构和变迁。本文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梳理中国慈善观念由“善举”到“慈善”、由“义行”到“公益”的历史轨迹,探寻了中国历代慈善公益文化的丰富资源,描绘了源自西方的慈善公益文化在近代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慈善公益文化相汇流之后呈现出的独特面貌,对近代时期“慈善”、“公益”等观念的形成及其变迁进行了梳理,值得当代中国的公益从业者参考。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曾桂林
2017年8月,徐永光先生出版了新著《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他在书中首先重构了一张公益与商业关系的光谱图,以此为基础提出公益也是一种“市场”,它应该向右,再向右,转变为商业模式,成为社会企业,进而主张公益市场化,反对公益行政化、公益道德化。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观点很快引发业界对公益、道德及商业等相关问题的热烈探讨,其中康晓光先生的书评尤为尖锐,随即徐永光先生又予以辩驳,有论者称之为“二光之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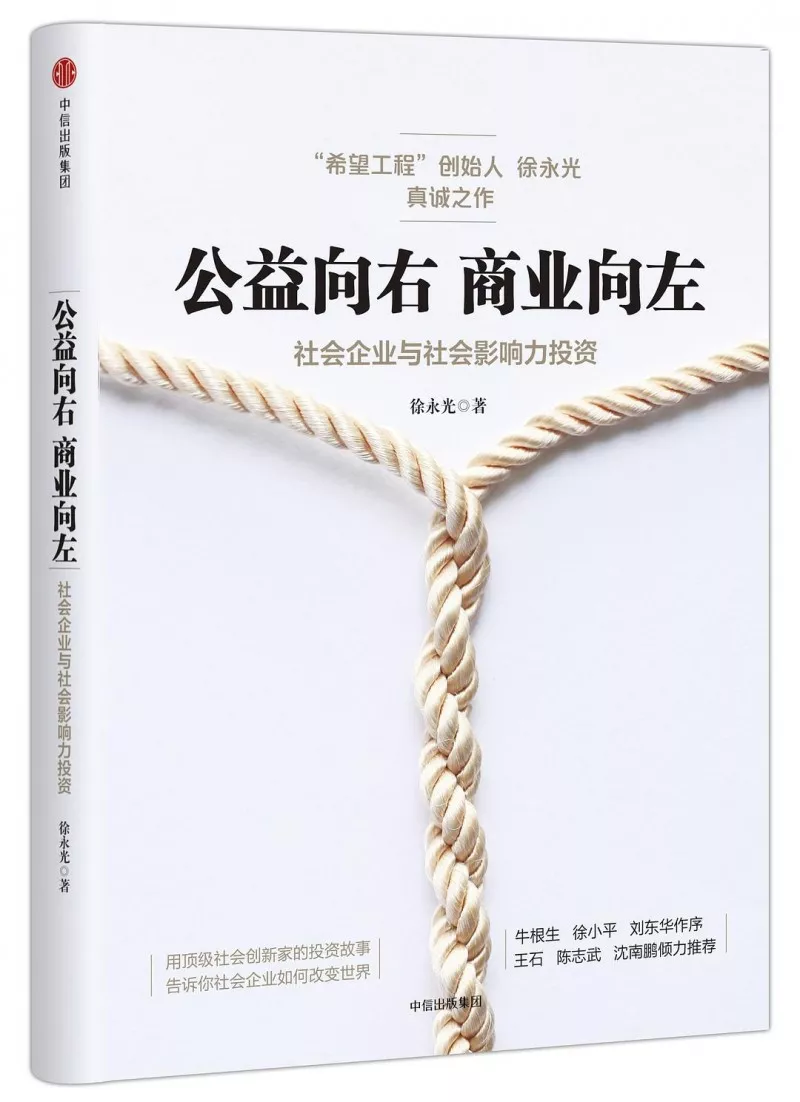
以上问题的凸显,或许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当代中国在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围绕慈善公益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以及面临着在西方慈善公益理论、中国本土语境和历史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纠葛。当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复苏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亟须根据时代命题,更新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审视自己的新定位。 看清来时的路,才能走好前方的路。我们知道,现代慈善公益观念源自西方世界,其本身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它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重构与变迁。由此,本文拟重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对近代时期“慈善”、“公益”等观念的形成及其变迁进行一番梳理。
从“善举”到“慈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仁爱、民本及大同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的重要源头。两汉之际,随着道教的创立、佛教的东传,善恶报应、积德行善、因缘业报及慈悲观等宗教教义也构成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慈善文化。可以说,儒、佛、道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慈善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宋明以后,儒释道三教出现合流趋势,善书运动蓬勃兴起,加上社会因素等诸合力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不断趋向兴盛。
不过,中国古代慈善事业虽很发达、很兴盛,却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清末光绪年间以前,尚无“慈善事业”这一词汇,类此行为多称为“善举”。“慈善”、“慈善事业”等概念,是清末才出现并普遍使用的。
实际上,随着魏晋南北朝佛教广泛流布,汉译佛经极为盛行,《大方便佛报恩经》、《菩萨本缘经》、《长阿含经》等多部佛经已出现“慈善”语汇,诸如“慈善根力”、“佛以慈善,教化一切”、“怀怖畏心,发慈善言”等。而约于3世纪译成汉文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慈善”,可能是最早的合成词例。由此而见,“慈善”一词的出现或形成,与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并得到广泛流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慈善”首见于佛教经典,但慈善思想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儒家所言的“仁”、“义”、“仁爱”、“大同”等,而佛教的东传及其本土化,又摄儒入佛,与中国社会原有的慈善思想相互吸纳融合,汇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底蕴丰厚的慈善文化的活水源头。
梳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经历先秦时期的滥觞期后,至两汉魏晋南北朝迎来了一个初兴期,佛教慈善活动甚为活跃,除济贫赈灾、施医给药之外,还规诫杀戮、劝善修德,广泛进行财布施、法布施。这一时期出现的早期慈善设施与制度——给孤独园、六疾馆以及僧祇户,都与佛教息息相关。而这些慈善设施,下启唐代悲田养病坊、宋代福田院等常设性慈善机构,从而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善堂善会也日久弊生,出现经费不足、管理混乱、堂屋损毁等情形,总体上呈现出衰落之势。再加之这些传统善堂善会多重养而轻教,救助方法消极,因而常为时人所指摘。在急剧的近代社会变迁中,西方慈善事业伴随着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而渐次展开,先后举办了慈善医院、育婴堂、孤儿院、赈灾会等慈善组织或慈善机构。甲午战争前后,在西方慈善事业的影响下,改良中国传统善堂善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迫切希望教养兼施,并在收养对象、管理运作等方面进行改革。
梁其姿曾指出,明清之际善会善堂作为整顿社会秩序的策略,其所救济的对象并非所有生活困苦的人,而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的。如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组织同善会就明确规定,不救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游手好闲者,此外,还有四种人“宜助而不助”,即衙门中人、僧道、屠户及败家子等。后来创设的普济堂、清节堂、恤嫠会等善堂善会,也带有救济道德化的倾向。然而,鸦片战争后贫民、流民越来越多,但善堂善会救助对象仍多限于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人群,且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方可收养,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救助的需要,而西方国家的救助范围则更为广泛,贫民、流丐乃至妓女、罪犯、受伤士兵等均属救济之列。
此外,在时人眼里,中西方的救济动机不同,救济制度与方法也不一样。首先,中国的“善举”是种德积福的行为,其动机源于积善余庆、为善必有善报的观念,难免带有利己主义的色彩;而欧美各国的新“善举”则尊奉上帝旨意,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用人道、博爱的精神来撒播福音,解救他人苦难,完成助人之举。其次,在救济制度与方法上,中国善堂善会大抵为施衣给食,大抵为消极的施舍,所谓“养”则有之而“教”不备,救助层次相对较低;西方慈善组织的着眼点在于消除人们致贫的根源,讲求救人救彻,对受助者养教兼施,采取积极救助方式,即在收养之余,往往还会传授文化知识和培训工艺技能,使受助者数年后能有一技之长,自立谋生。也就是不单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
两相比较,近代西方的慈善事业似乎更为优秀、先进,而中国传统的善举则屈居次等了,这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人对中西慈善事业的一个基本观感。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善会善堂“近代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
随着西方慈善思想的传播以及“慈善”、“慈善事业”新概念的引介、普及,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善堂善会)也在发生着改变,逐渐突破传统道德的限制,扩大救助对象与范围。误入歧途的失足者、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妓女等人也被纳入救助之列,洗心局、迁善局、丐所、济良局、工艺局、习艺所、因利局、劝工场等各种新式的慈善机构纷纷涌现。
从“义行”到公益
所谓“公益”,顾名思义,是指公共利益,它也是一个从近代西方引介进来的新名词。然而,“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与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不同,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公益也与西方、尤其是与中世纪西方大不相同”。由此,基于传统社会内部产生、演变而来的公益,中国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公益”这一近代术语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公益的概念,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或事物,人们常以“义”名之,如“义学”、“义塾”、“义仓”、“义井”、“义浆”、“义田”、“义庄”、“义冢”等,并把此类行为统称为“义行”或“义举”。其中,这些公益设施很多都是私人共同捐资举办的,如“义学”、“义仓”、“义米”等,而“义庄”、“义田”多为宗族慈善机构,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明清义庄
在中国古代,这些公益性组织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即教缘性的佛教社邑、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会馆、业缘性的公所。
据敦煌文书所载,魏晋至隋唐五代间,西北地区出现了为某种公共事务结成的民间团体,即社邑,尤以普通百姓组成的私社最为活跃,大抵为丧葬互助、共济急难、立窟造像及修渠建堰、架设桥梁等公益活动。这些社邑平时有“义聚”,即为公益积累,以备赈济,遇事再临时捐助饼、粟等物品。社邑虽因佛事而聚集在一起,但其世俗色彩也很明显。社员通过捐助与纳赠筹集资财,用于一家一户难以应付的佛事、丧葬、水利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以至民间信贷合作互助。到唐代,这种民间公益团体的社邑发展到鼎盛期。后因武宗废佛,社邑遭到限制与打击,渐趋衰落。
此外,佛教寺院及佛僧在济贫渡人等善举之外,也举办多种公益活动,如设无尽藏、药局、筹划地方公共工程等,如建桥修路。两宋时期,福建、浙江等地佛僧造桥数量极多,规模也甚宏大。还有设亭阁,施茶水以利行人的。宋代,范仲淹首创的苏州范氏义庄,救济族中贫困者,婚丧嫁娶及入塾中举均有资助,延续八百多年。这对后世民间宗族公益事业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至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义庄极为盛行,各府县少则数十、多达上百处,著名的有苏州潘氏松鳞义庄、丰豫义庄、留园义庄、无锡华氏义庄等。作为血缘性的宗族公益设施,义庄义田以救济族中贫困者为宗旨,也有由族内推及族外,乃至社区邻里的,如丰豫义庄。
会馆为地缘性的公益设施,明清时期十分普遍,最初为士子赴京城、省会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栖息之便,清代各大都会商埠也有些商业会馆,但仍以省府县籍为主,面向同籍官绅商民开展联谊叙旧、济贫助困、施棺助葬等公益活动。像上海、苏州、北京、汉口、扬州等地都是会馆云集之地,其公益活动甚为频繁。清中后期,一些繁华的省会城市,百商汇聚,一些商人会馆演变而成专门性的商业公所,则主要为同业、同籍商人的公益活动,既有面向商人内部的,也有赞襄社会公益活动的。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国家组织形态较为成熟,官府的影响下渗至基层,保甲乡约制盛行,由此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控制严密,民间公共领域虽存在公益活动,但整体上并不是十分活跃。但及至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西方公益事业及其观念东渐,于是晚清中国便出现了“小共同体”与“社会”同时觉醒,即所谓“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秦晖在对中西公益事业史进行比较研究时,即注意到这种奇特的公益景观。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湖南长沙创设南学会,其所拟章程十二条,其一即揭橥“本学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另外,按察使黄遵宪等人设有保卫局,“且保卫局系属公益,断不责令一人一家,独捐巨款。其同受保卫局必益者,亦未便听某人某户不出一钱”。可见,戊戌年间,“公益”观念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了。
至19、20世纪之交,“公益”一词更为国人所熟知,报刊载论更盈于耳目。据1899年《申报》载称,俄国欲攫取的中东铁路“在清国为至大之公益事业”;论及德国商务发达情形时,在列举各行各业的数据后,还提到“其余浴场、病院、养育所、学校、剧场、博物院及公益慈惠事业之动物园、旅馆、酒店等为合股而成者,统计三百五十所”。同时还认为,在西方国家,开矿、筑路、博览会均为公益之事。社会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以其能保公共之利益也。有公益者为社会,无公益者非社会,故夫一社会之中通力合作,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互为团结,互为保护,斯不愧社会之名称”。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近代公益实际上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民主主义的传播以及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源自西方的“公益”更多从权利意识方面主张,更多的是利益诉求。由此,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渐趋消解,兴办实业也便成为晚清绅商颇为关注乃至热衷的公益事业。清末状元张謇,就在民族危亡之际,践行实业救国,在创办大生纱厂稍有赢利之后,自1904年开始在南通相继创办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以及一系列学校,还兴建起医院、贫民工场、养老院等公益机构,至民国初年已初具规模。后来,张謇回忆说:“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1905年,清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公益也是地方自治筹备事项的重要内容,热心公益成为地方选举绅董的一个重要条件。 “若夫为董事者,兴公利,谋公益,群情通而团体,固以立祖国文明之基础”,实为荣誉之至。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列自治事项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营业,各项所含具体名目大都与公益相关。由此而见,较之古代社会,晚清中国的公益范畴已大大扩展了。很快,各地纷纷设立自治公所,一些善堂善会、会馆公所的董事,成为新式公益团体的发起者或组织者,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自治之权,竭力扩充新的公益活动,以裨益于社会。
除上海、天津、广州等大都会之外,南通的公益事业也表现最为显眼,这与张謇个人因素有关。张謇多次表示,兴办实业赢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强国富民。故而,他为纱厂取名“大生”,即源于《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纱厂开办之初,他在厂约中规定,每年余利,除提保险公积、派分股红外,还需留一定比例充作善举、补助公益之用。
这从大生企业集团的历届账簿中清晰可见。有经济史研究专家指出,在1926年张謇逝世前,大生资本集团一厂利润分配中用于赞助公益事业的部分,总计69.11万两,占实际利润分配总额的5.46%。其中,大生纱厂自创立后的二十余年间(1900〜1926),对通州师范等学校的资助累计27.92万两,占赞助公益支出的40.4%;其次是育婴堂、养老院、医院以及浚河筑堤、修路架桥等慈善公益事业,计9.71万两,占14.06%;再次是赈灾救济,计6.08万两,占8.79%;其余25.4万两用于地方社会的其他公共事业开支,占36.75%。 此外,南通博物苑、更俗剧场、纺织专门学校等公益机构,其大部分经费也来源于张氏所创办的企业。
这是张謇的儒商性格所使然,体现出他为“儒者的本分”。换言之,若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张謇作为状元实业家,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意欲切实担当起“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而其所创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完全成为了一个社会企业,南通也成为近代中国“模范第一城”。

南通被称为“近代第一城”
结语
纵观“慈善”、“公益”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虽然已有其名,但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慈善公益事业,而是在中国语境之下承袭了传统的善堂善会的精蕴的同时,也应时而变,吸纳了西方传播而来的某些因素,从而发生了重组与变构,呈现出与西方慈善公益不尽相同的面目。这主要原因在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基于儒家文化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迁,宗法制度依然顽强地存在,并未形成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会、社区及平等、民主权利而产生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格局,因而“慈善”、“公益”在现代形塑中也就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现代慈善公益是当今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当代中国公民理应热情地呼唤现代慈善公益,努力推进现代慈善公益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现代慈善公益是由传统慈善公益发展而来,而后者又与中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是我们中国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传统慈善文化的源泉。我们更要明白,现代公益的发展,除了吸纳融合人类共同富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亦应该从本土语境及文化传统中寻找动力源。唯有如此,现代慈善公益事业才会健康地发展,并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