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里的晚清:从众声喧哗到千夫所指
来源:史客
1901年:
“维新”再成流行词
“帕尔森从他自身的例子说明清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有一个陪同他的大清官员询问他,是否应该将两个儿子送出去接受西式的教育?” 1901年2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工程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观察笔记》说,粤汉铁路技术总监帕尔森认为,“现代化的教育将横扫一切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由于统治阶级无能而造成的种种痼疾正催生着一场激进的变革”。
变革之声,自1840年以降,不绝于耳。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年,《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主笔王韬希望中国一改因循之弊,除旧革新,实现由弱到强的循环。他在报上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

王韬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商办,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废八股,改科举,以有用之学选拔人才;政府必须倾听民众声音,让民众讲话。开创文人论政新样式的王韬,发出近代中国维新先声。
洋务运动,中国有了铁路,有了钢铁厂,有了军工厂,有了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还是败了。
人心思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来临。3年内,各地共有近60家民间报刊面世,大多主张维新,重视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绍。
报业初兴,舆论渐开,维新观念渐入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7月的一道上谕说:“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时势所至,一个“言论界之骄子”横空出世。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大力鼓吹变法。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种“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读者耳目一新,舆论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评说:“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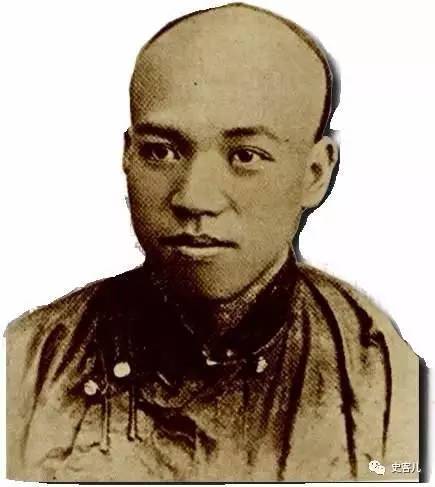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赞助,他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不过,一旦他认为《时务报》的政论出格,比如“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语,又施压干涉——政治体制红线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就定下了“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权力不能变。因此,张之洞要在《劝学篇》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称改革的洋务运动,也就只能务,不能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旨将全国报馆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谕旨称:“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统治者一句话,救国心切的报人就成了造谣惑世的斯文败类。除几家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被迫停刊,人员外逃。
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进京围攻洋人,八国联军打来,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
庚子之耻刺痛了国人,无论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还是各地官绅,都发出要求朝廷变革的声音。一时间,“人人欲避顽固之名”,戊戌之后,“维新”再度成为流行词。
大势之下,慈禧不得不启动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表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上谕强调,“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在“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多个层面变法。
很多人认为慈禧只是做秀糊弄人,就连“体制内”也有人这么看,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友人说:“日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
作为新政措施第一条,朝廷废除了满汉不得通婚的禁令。第二步是教育:科考取消八股文并最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各地设新式学堂,官费留学生规模扩大。
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在“体制内”首倡君主立宪:“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不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
开报禁的呼声在朝野间响起。1901年底,各地报刊恢复到34种。
这一年,中国出现了首位当众演讲的女性。在上海一个集会上,16岁姑娘薛锦琴自告奋勇上台演讲,号召国人阻止俄国人占领东北,反对清廷和俄国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此事经报道,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
这一年,官员们纷纷出国开洋荤。去日本的官员们借考察之名吃喝玩乐,丑态百出,被国内报纸揭露,激起公愤。屡试不第的江苏人李伯元从仕途梦中醒转过来,开始写《官场现形记》。
论战:
改良还是革命?
1902年2月8日,日本横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他在创刊词中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的《新民说》在《新民丛报》连载近四年,阐明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引进了国民、权利、自由等汉语新词汇,呼唤独立人格的一代新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亟需启蒙。对于政治制度,他主张渐进改良,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
虽被清廷严禁,《新民丛报》仍在国内一纸风行。梁启超后来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丛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常识,正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匮乏物。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宗旨是“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创刊之初,《大公报》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于被囚瀛台的光绪,指斥新政名不符实。同时,宣扬“立宪法,予民权”,希望清政府在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真正的改革,变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于上海。该报大量介绍西方宪政学说,并进行中西政治比较:用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批判中国的君上大权;以西方政党内阁的政治稳定性,对照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动荡;从西方的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谈到“中国人民踡服于专制政体之下”无人格无权利的奴隶地位。这是报纸上的公民课。
这边厢,改良派报刊鼓吹君主立宪;那边厢,革命派报刊高呼“革命其可免乎”。
且看当时多在海外创办的革命派报刊言论:
香港《中国日报》:“国与朝廷判然为二物。”
日本横滨《开智录》:“灭此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
日本东京《国民报》:“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
上海《中国白话报》:“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排满。”
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寿期间,上海《警钟日报》发表了一副林白水写的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出了创刊号,提出六条宣传纲领: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公开陈述三民主义。
《民报》创刊时,改良、革命两大阵营已成水火之势。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两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去向的大论战。
论战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二、革命会不会导致内乱?
三、革命会不会导致专制,革命后能否成功建立共和政体?
四、土地国有是福祉还是祸根?
随着论战深入,梁启超渐显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民报》声势占了上风,时势发展下人心向背使然——清廷的败坏日甚一日,梁启超实在难以维护,他痛心于“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倾向革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学者高一涵回忆:“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1907年8月,《新民丛报》悄然停刊,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论战终告结束。论战使国人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政治新观念,曾参与两派调停的徐佛苏评说,“诚足以开我国数千年政治学案上之一新纪元”。
这场论战,注定没有结论。改良与革命的选择,自此考验每一个中国人。
启蒙:
当舆论唤醒人心
1907年7月15日晨,浙江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各地报纸迅即将报道重心移向秋瑾案,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论。报界一致同情秋瑾,斥责官方在没有秋瑾确供的情况下就杀害她,对官府的办案细节处处质疑。

从秋瑾案出发,抨击人治,呼唤法治,《申报》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音。
众声喧哗的时代,《申报》的同行们皆不示弱,大胆发言。
《时报》表示,秋瑾之死“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大公报》、《神州日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等接连发表评论,痛惜秋瑾“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痛斥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是“恶魔政治”。
1907年10月31日,《时报》报道:“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杀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良知未泯的李钟岳因对此案处理持反对意见被撤职,他作为案件具体执行人,内疚之情无以复加。
“专制时代良吏”,这是当时舆论对李钟岳的一致评价。

而杀害秋瑾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标统李益智等人,受到舆论围攻,威信扫地,如丧家之犬。张曾扬拟调任江苏巡抚,遭到江苏士绅集体抵制。清廷让步,将他转调山西。《时报》报道,张曾扬离开杭州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弟弟秋宗章叹道:“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对于秋瑾遇害后的公愤,有人说,“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有人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学者夏晓虹认为,“此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虽源自其乡前辈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论,却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
观念转型,远比制度转型艰巨漫长。“开民智”成为晚清知识阶层的口头禅。
彭翼仲于1904年在北京创办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社会启蒙实验:反对陋习,提倡新风,热心公益事业;开放式办报,与读者互动,成为“公众言论机关”;通过阅报处、讲报所,让更多不识字的人了解新闻和新知;倡导戏曲改良,演出有益世道人心的新戏;声称“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叫人人知道爱国”,发起国民捐运动;反对强权,表明“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亡朝廷不能算亡国家”。
据说,“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有御史奏称,京城社会曾异常闭塞,《京话日报》创办后,“风气逐渐开通”。
1907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社论《觉醒的中国》说到中国的新思潮:“这种民族思潮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国乃我中国人之中国。”
共鸣:
向皇权要宪政
慈禧新政措施,多未落实。张之洞失望地说:“京朝门户已成,废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债重,民愈怒。”
为了缓和排满气氛,清廷多次声称并无内满外汉之意,又颁行《劝善歌》,颂扬“德政”,却未收到丝毫效果。
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04年张謇说服张之洞奏请立宪,以自制《日本宪法》送到内廷,并印行其所著《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也请定宪法,津沪报刊纷纷响应。舆论认为立宪足以致强,不容置疑。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出告终,震动中国朝野。人们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的优劣联系在一起,认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考察报告指出:“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
立宪派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立宪团体,创办新报刊,呼吁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改革方案。
然而,现实给立宪派兜头一盆冷水。
预备立宪先从“厘定官制”入手。官制改革之初,慈禧宣布“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回避改革核心问题的“五不议”一出,众人心凉了半截。徐佛苏道:“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官制改革徒有其名,几成闹剧。《时报》评论说,这是“假立宪之名,阴行专制之伎俩”。
看出清廷并无立宪诚意的立宪派,号召各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新报》开始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其他报刊跟进,鼓吹速开国会,“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
从1908年到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都派代表进京递请愿书,上百万群众参加签名和集会游行,学生罢课响应,报界推波助澜,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天津一位店员表示:“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
第三次请愿时,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并上奏。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
迫于形势,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5年,同时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命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与此同时,清廷强令各省举行拥护朝廷5年立宪决策的庆祝活动。在官方的组织下,各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群众演员高唱爱国歌曲,三呼万岁。
梁启超愤懑而绝望:“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自称这个时期“无日不与政府宣战”的梁启超摞下狠话:“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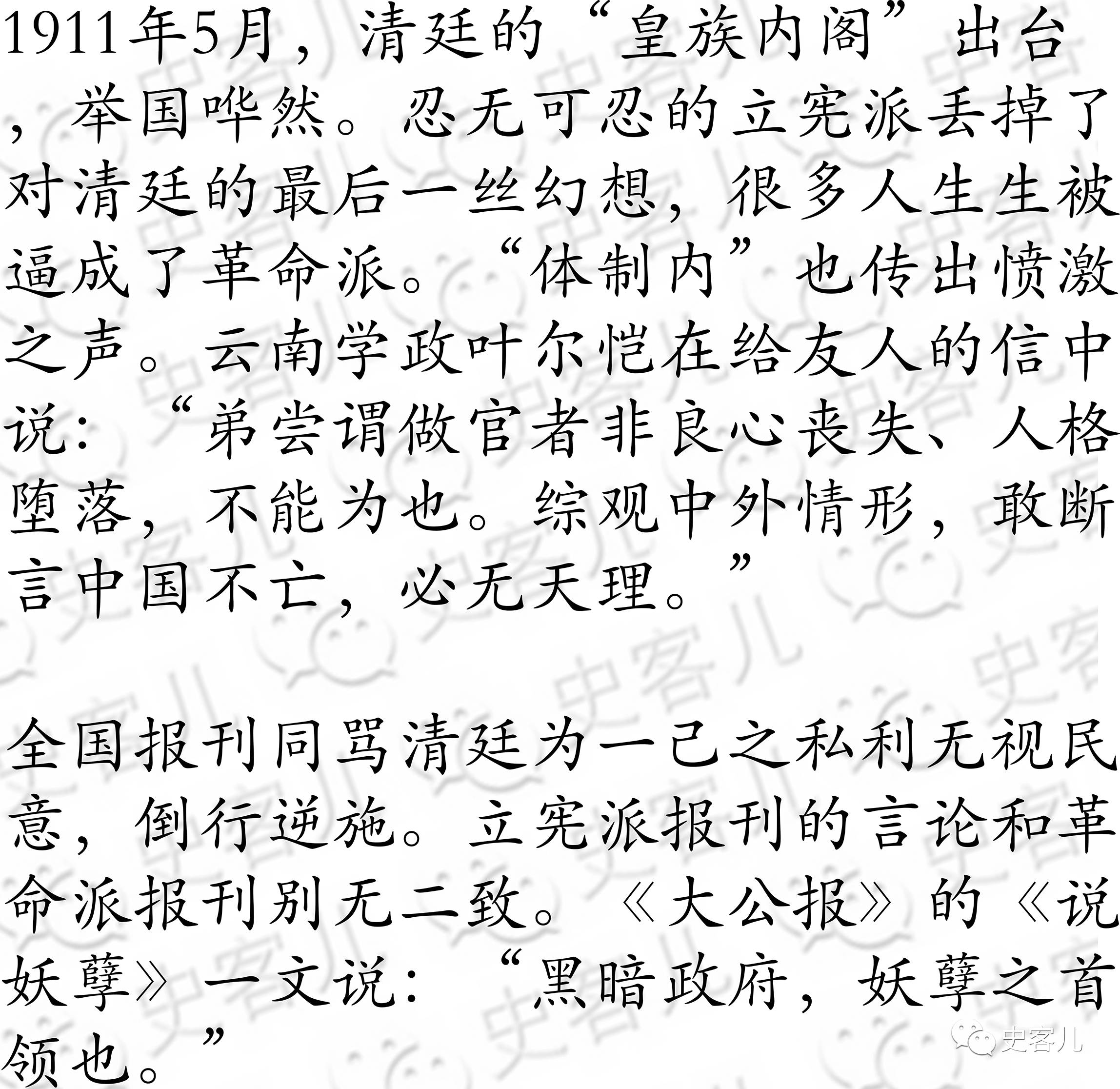
全国报刊无日不与政府宣战,一起为一个黑暗政府送终。
1911年10月中旬,《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在北京王府井的居所每天门庭若市,很多人来找这位消息灵通人士了解武昌起义的情况。莫里循给朋友的信中说:“我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
1911年11月17日,以译著《天演论》影响过一代人的严复给莫里循写了一封长信。办过《国闻报》的严复敌视革命,他在信中强调,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
当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此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每天人山人海,人们挤在各家报馆的贴报栏前看报纸上的革命军消息,捷报传来,一片欢呼。
孙中山感慨:“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
喧哗与骚动过后,孙中山提出,新闻就是通过宣传“纠正人心”,报纸理应是“党的喉舌”,党报应用“正确之真理”同化“不正当之舆论”。
孙中山的口号是:舆论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