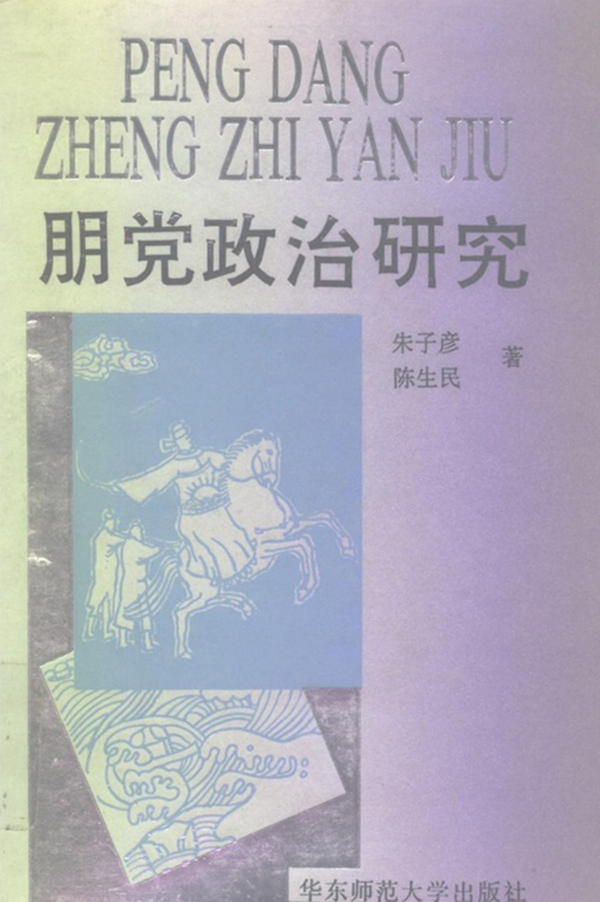“宁负朝廷,不负朋党”:中国历史上的朋党
作者:程念祺
|
|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8月出版,593页,75.00元。
治中国政治史,“朋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以“朋党史”为专题研究的,并不多见。我们过去研究“朋党”,往往只注重历史上官僚士大夫“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的一面。然而,“朋比为奸”与“党同伐异”,岂止官僚士大夫如此!在中国官僚政治的框架中,官场上,除了官僚士大夫的朋党,也还有种种因身份、特权而结成的各类朋党。朱子彦教授继其《朋党政治研究》(与陈生民合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而作《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做了广泛而长时段的考察,将朋党研究的视野,从仅仅关注官僚士大夫阶层,放宽到历史上的整个统治阶级,从而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官僚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朋党古已有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宦)党、奸党”均为其属;而且,都是出于利益之争,而无君子小人之别。因此,作者不同意欧阳修《朋党论》中关于朋党尚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的观点,认为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终将导致“党同伐异”。
|
|
《朋党政治研究》
对朋党作这样的判断,与作者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的基本估计有关。作者强调,尽管有时“党争也有邪正是非之分”,“不宜一笔抹杀”,何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一定都构成朋党斗争,但是,朋党斗争却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则是毫无疑义的”。以“各类朋党素描”为题,作者在本书导言中,对中国历史上各类朋党的特点作了一个概略的呈现:
就朋党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群体结合的凝聚力”之问题,作者从家族宗法、乡土观念以及封闭地域中的心理认同这几个方面入手,指出:“封闭的地域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本身就是小农经济结构的产物,这些人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就必然把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带入官场之中,按照他们的籍贯以及政治上的一致性而结成帮派体系。加之官场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同籍官员也就以血缘和地缘为互相联络、朋比党援的纽带,形成政治上的地域性分野。封建官僚的地域性分野一旦形成,也就必然导致朋党门户之争的不断爆发。”
就朋党争斗中形成的“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之问题,作者则抓住了南北士族势力的此消彼长;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明清时代朋党结合的纽带——乡里、科举同年或门生座师、儿女姻亲;以及南北官僚势力平衡的最终打破;南方士人集团优势的形成诸问题,对历史上朋党斗争的利益关系作了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势力由北强南弱,转变为南强北弱过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就朋党在官场上“结党贪污,败坏吏治”之问题,作者以朱元璋的“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话头为题,引章学诚“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而谋十万金之利”语,以具体的史料说明“不少官员一到任所,便大力网罗党羽,往往在本衙门内大量扩充书吏、衙役的人数,将许多”顽恶泼皮”、社会渣滓委充吏役,收为己用”,“他们”在乡结党害民,议受赃私,密谋科敛,夤缘作弊”,“这些人勾结起来,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为一股拥有很大势力、具有很大能量的地方性恶势力”的历史现象,由此揭示了“官僚集团比官员个人的贪污能量要大得多”;“结党贪污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奉行的准则是“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皇权真正顾忌的是朋党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而”富有天下”,将整个国家都视为自己的私产,而为其服务的官僚集团也同样要分享这种权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并指出官僚贪污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导言最后以王夫之所谓“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为题,论“国无党祸而不亡”的道理。作者认为,“朋党政治中的官僚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迎送、参谒、馈送来维系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帮衬,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奥援,徇情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从根本上“导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朽,吏治的极端腐败”;“朋党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必然“使历代君主颇为痛恨”;而“进步、革新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他们各立门户,附己者则善,异己者则恶,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党同伐异的传统窠臼,因此新旧党争也往往以朋党斗争的形式出现”。
在导言所呈现的上述中国历史上朋党之争的问题中,作者逐章讨论了自先秦到明清的朋党争斗的特点。其研究的方法,是将个案分析与时代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作者坦陈自己“对东汉、三国及明代的党争着墨较多,用力较勤”。但通观全书,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既有具体分析,又有整体性把握。比如,对于北宋时期因变法而形成的新旧党之争,作者在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对于民国学者王桐龄将当时“新旧党倾轧之祸”一概归之于“意气相竞”的意见是否定的,而认为庆历至熙丰时期新旧党“确实围绕着北宋王朝是否需要变革而展开斗争,与”意气相竞”毫无关联”,“元祐之后的新旧党争才算得上”无智愚贤不肖,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而难有是非曲直之分”。作者还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强调“恪守传统的思想观念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同时还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观念之中,凝结、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里”;一方面又强调使旧党“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规模地改革旧制,就会损害他们的许多特权”,并引严复“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的道理,以说明后来的新党之中布满小人,亦皆唯利是图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们“得志便猖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而对“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朋党之争的性质作了深刻揭露。
明朝灭亡的时候,有人哀叹:过去“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梁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族类共天下”,而明朝没有这些问题,是皇帝乾纲独断,又怎么也会弄到亡国的呢!读此《中国朋党史》,我们就可以明白清楚地知道,历朝得与帝王“共天下”者,都不过是朋党。明朝的皇帝虽不欲不与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宫奴(宦官)和家臣(内阁大学士)直接控制政府,结果却是党争之盛,旷古所未有。盖皇权越是专制,执行者就越是权重;执行者越是权重,也就越倾向于结党营私,以至于朋党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你死我活。你看明末的时候,不仅士大夫各皆为朋党,后来甚至与宦官结成了阉党。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于他们心中“有朋党而无是非”。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因权力失衡而引发爆炸性的利益冲突,“宁负朝廷,不负朋党”,就成为朋党斗争的唯一选择。总而言之,朋党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权力越是专制,朋党斗争就越是厉害。
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斗争,一方面固然是皇权专制的必然产物,其激烈程度亦与皇权专制的程度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即当这种斗争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反过来削弱皇权,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皇权崩溃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朱子彦先生的这部《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朋党斗争的来龙去脉、各时期因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而形成的朋党斗争的特点,以及皇权不断强化与朋党斗争之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具体而深入的解释。它不仅对以往中国历史上朋党问题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亦将这一研究整体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