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一定是“朕”,朕却一定是皇帝
文/赖正直
在现代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皇帝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都自称为“朕”,仿佛皇帝除了“朕”就不能自称别的了。但实际上,只要我们在读史书时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发现古代的皇帝在许多场合、许多情况下并不自称为“朕”,而是和平常百姓一样自称为“吾”、“我”等等。究竟皇帝在什么情况下自称“朕”,什么情况下自称“吾”、“我”?
今天我们来试做一个简单的考证。
1
秦汉时期:书面须称“朕”,口头可用“吾”
“朕”作为皇帝专用的自称,始于秦始皇。在秦始皇之前,“朕”是一个人人皆可使用的自称,例如屈原《离骚》一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当然,这个时候的“朕”虽然人人可用,但它是非常古雅的一种称呼,仅在《离骚》这样的相当正式的文学作品中使用,一般人在平常说话时大概不会自称为“朕”。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奏:“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秦始皇除了把“泰皇”改为“皇帝”外,同意了李斯等人的其他意见,也就是同意天子自称为“朕”。从此“朕”就成了皇帝专用的自称,其他人不能用。

但“朕”只能由皇帝自称,并不意味着皇帝只能自称“朕”。即使是称“朕”第一人的秦始皇,有时候也没有自称“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等人逃亡后,秦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在这里,秦始皇自称为“吾”、“我”,并不自称“朕”。
秦二世也和他父亲一样,有时自称“朕”,有时称“吾”。
据《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即位后,召赵高谋事,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我个人分析,李斯等人上奏的皇帝自称“朕”的制度,主要是用于官方正式文件的书面语,带有一种端着架子说话的生硬语气,其实就是装逼。当皇帝自称“朕”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庄严、权威,说话是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命令式口气。因此,在平时的日常说话里,如果是比较严肃的场合,皇帝也可以自称“朕”,但如果是比较随意的场合,就不太适宜自称“朕”,而要用“吾”、“我”等普通的自称。
正确用法示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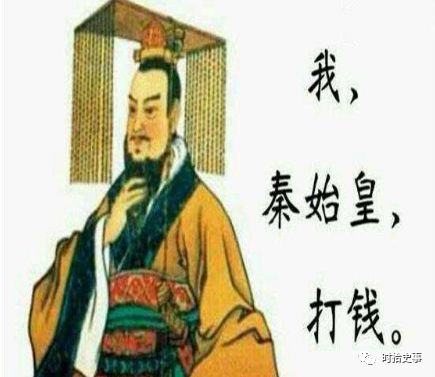
例如上述秦始皇得知方士逃亡,是面对身边的近臣,且在盛怒之下情不自禁说出了“吾”的自称,而秦二世称“吾”也是面对赵高这一极为亲密的宠臣,是在比较随意的场合,谈论的也是“耳目之所好”等轻松的内容,因此他不自称“朕”,而是自称“吾”。
秦朝的这一称谓制度沿袭到了汉朝。也就是,在诏书等正式书面场合自称“朕”,平时则视情况自称“朕”或“吾”。
例如《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文帝即位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汉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这些皇帝自称“朕”的诏书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皇帝自称“吾”、“我”的记载。
例如《史记·封禅书》载,汉高祖刘邦问群臣:“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众人不能回答。汉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问群臣:“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
《汉书·周勃传》载,周亚夫之子盗卖官器被问罪,周亚夫也被牵连。汉景帝命令廷尉让周亚夫作出书面解释,周亚夫拒绝。汉景帝大骂:“吾不用也。”(意思是我不用你解释,我直接把你抓起来)。
这里的汉高祖、汉武帝问的是神仙鬼怪之事,是非正式的说话场合,所以他们都说“吾”。汉景帝是骂人,当然也不适宜用端庄的“朕”,而是称“吾”。

司马迁曾经当过中书令,班固曾经当过兰台令史,二人都曾有机会经常和皇帝面对面谈话,而且《史记》、《汉书》文风朴实,都是用当时的日常用语写成的,纪实性很强。《史记》、《汉书》中记载的皇帝自称“吾”的情况,应该是贴近实际的。
在汉朝还有一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就是皇帝在同一场合说话时,一会儿用“朕”,一会儿用“吾”。
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即位后,置酒雒阳南宫,汉高祖问群臣:“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汉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是酒宴的场合,本应是轻松随意的,但汉高祖前面自称“朕”,后面又自称“吾”。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汉光武帝对严光说:“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不久之后,他又问严光:“朕何如昔时?”
同样是面对好朋友严光,但汉光武帝时而称“我”,时而称“朕”。估计是这一时期在皇帝的口头语中“朕”和“吾”并不严格区分,皇帝怎么用都不算过分。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吾”的情况增多
进入三国时期,乃至此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自称“吾”的情况比秦汉时期更为增多。具体表现,一是皇帝在口语中自称“吾”的例子更加常见,二是某些皇帝在诏书、敕令中也自称“吾”而不自称“朕”。这可能是由于庶民出身的皇帝大量出现,很多皇帝即位时已经是中老年,他们不太习惯自称“朕”,或者是一时改不过口来吧。
刘备比较严格地遵守了汉朝遗留下来的制度,书面称“朕”,口头称“吾”。
例如《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遗诏敕太子刘禅:“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同时,对在身边的鲁王刘永说:“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刘备在遗诏中使用书面语“朕”,但在和儿子面对面说话时则使用“吾”,分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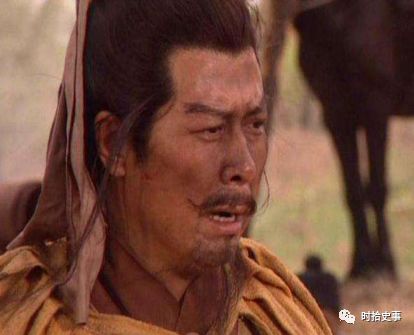
但曹丕就比较皮了。他不按汉朝的牌理出牌,不但在口头语里面自称“吾”,在有些诏书里也自称“吾”而不自称“朕”。
《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曹丕《癸酉诏》曰:“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同书载曹丕诏司马懿曰:“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
在这些诏书里,曹丕本应自称“朕”,但却自称为“吾”。不仅诏书,曹丕在写给孙权的信里也自称“吾”。
《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答书孙权:「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
曹丕的做法影响了他的继承者们。曹睿、曹芳都有在诏书、敕令等正式书面文件中自称“吾”的例子。

《三国志·明帝纪》载曹睿给淮南诸将的敕:“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孙)权走也。”
《三国志·三少帝纪》载齐王曹芳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
皇帝在书面语中自称“吾”的例子一直到南北朝仍不时出现。
《晋书·刘隗传》载,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晋元帝诏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
《宋书·戴法兴传》载,宋孝武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临万国,推心勋旧,著于遐迩。不谓戴法兴恃遇负恩,专作威福,冒宪黩货,号令自由,积衅累愆,遂至于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异同纷纠,非唯人情骇愕,亦玄象违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怀。吾今日亲览万机,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诚尽力,以副所期。”
《南齐书·柳世隆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敕柳世隆曰:“吾更历阳外城,若有贼至,即勒百姓守之,故应胜割弃也。”萧道成打算将东晋时侨置的南豫州与豫州合并,敕柳世隆曰:“比思江西萧索,二豫两办为难。议者多云省一足一于事为便。吾谓非乃乖谬。卿以为云何?可具以闻。”
《南齐书·张绪传》载,齐武帝萧赜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
这是书面语的情况,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口头自称“吾”、“我”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晋武帝问樊建,诸葛亮何许人,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晋武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晋书·张华传》载,张华主张伐吴而出军不利,贾充奏诛张华以谢天下,晋武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
《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将晋武帝比拟为东汉桓、灵二帝,晋武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
《晋书·郤诜传》载,郤诜在与晋武帝对话时自称“天下第一”,侍中奏免郤诜官,晋武帝曰:“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
《晋书·怀帝纪》载,典书令修肃与晋怀帝论时政方针,晋怀帝曰:“卿,吾之宋昌也。”
《晋书·恭帝纪》载,桓玄死后,其侄子桓振跃马奋戈,闯入宫中,谓晋安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晋安帝降阶下床,对桓振说:“此岂我兄弟意邪!”
《宋书·桓康传》在,宋武帝刘裕谓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正欲与卿先共灭虏耳。”
《宋书·张邵传》载,宋文帝刘义隆称赞张邵:“张邵可谓同我忧虑矣。”
《南齐书·明帝纪》载,太官进御食,有裹蒸,齐明帝萧鸾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
《南齐书·刘休传》载,尚书右丞荣彦远惧内,曾被老婆打伤,齐明帝对他说:“我为卿治之,何如?”
《南齐书·东昏侯纪》载,萧衍围攻建康,茹法珍跪求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出钱赏赐将士,以鼓舞士气,但萧宝卷说:“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
《梁书·简文帝纪》载,梁简文帝萧纲谓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梦吞土,卿试为我思之。”
《陈书·虞荔传》陈文帝要求到仲举举荐一名文学之士任掌书记,到仲举尚未回答,陈文帝曰:“吾自得之。”
《魏书·食货志》载,太安中,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
《魏书·尔朱荣传》载,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对尔朱荣说:“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岂信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自称“吾”、“我”的事例十分常见,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姑且不再赘述。
3
唐宋时期:用“朕”的情况增多
到了唐宋时期,皇帝自称“吾”、“我”的情况开始显著减少,不但在正式书面文件中自称“朕”,而且口语里面自称“朕”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但即使如此,皇帝在口语里自称“吾”、“我”的情况也还是大量存在,以下摘录一部分备考。
《新唐书·刘文静传》,唐高祖对刘文静说:“我虽应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无嫌。”
《旧唐书·高丽传》,李勣请求用高丽俘虏随军效力,唐太宗曰:“谁不欲尔之力,尔家悉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
《旧唐书·李勣传》载,李勣时遇暴疾,医者云,须灰可以疗之,唐太宗得知,乃自剪须,为其和药。李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又载,唐太宗寝疾,谓太子李治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
《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载,权臣史弘肇被杀后,后晋隐帝传语诸将:“弘肇等专权,使汝曹常忧横死,今日吾得为汝主矣!”
《宋史·石守信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与石守信等饮酒,酒酣,宋太祖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宋史·寇准传》,宋太宗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宋太宗闻之不悦,召寇准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以上所引唐宋皇帝自称“吾”、“我”的情况仍然很多,但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频度已经明显减少。

4
元明清时期:主要用“朕”,偶尔用“吾”、“我”
元明清时期,皇帝自称“朕”就更加常见了,使用“吾”、“我”的情况虽然还是存在,但与唐宋时期相比又进一步地减少了。以下摘录几例皇帝自称“吾”、“我”的例子。
《元史·世祖纪》,有回回因饮食习惯与他人发生纠纷,元世祖忽必烈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
《元史·后妃传》,元军灭宋,元世祖举行大宴,众皆欢喜,唯察必皇后不乐。元世祖问道:“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独不乐,何耶?”
《明史·刘基传》,明太祖朱元璋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刘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太祖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明史·西域传》,朝臣讨论乌斯藏来朝问题,明太祖曰:“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
《明史·沐英传》,沐英之子沐春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群臣请试职,明太祖曰:“儿,我家人,勿试也。”
《明史·于谦传》,有人上奏弹劾于谦,明景帝以其奏授于谦,于谦叩头谢罪,明景帝曰:“吾自知卿,何谢为?”
至于清朝皇帝自称“吾”、“我”的事例,在《清史稿》中几乎没有。《清史稿》里皇帝都是自称为“朕”。但考虑到《清史稿》的文风,经过编撰者修辞润饰的痕迹十分明显,不能反映当时人们说话的真实情况,因而不能据此断定清朝皇帝不分场合一概自称“朕”。

皇帝自称“朕”,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式用语,是君主至高权威的象征。因此,皇帝是否自称“朕”,不仅是皇帝个人的用语习惯或偏好,更是君主专制体制发展程度的体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体制,同时发明了皇帝在书面语中称“朕”,口头语中称“吾”的用法。
魏晋以来,由于政局动荡及士族门阀的兴起,君主权威相对衰落,君主专制程度较秦汉时期大大减弱,因而皇帝较少使用语气生硬的“朕”,而是放低姿态,多用平易近人的“吾”或“我”。唐宋时期,君主专制体制逐步恢复并完善,皇帝的权威空前提升,腰杆子也硬起来,因而能够经常自信满满地面对臣下自称为“朕”。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体制发展到了空前的全盛程度,因此皇帝称“朕”的场合也随之大大增多,只是偶尔在口头语中称“吾”或“我”。
皇帝自称“朕”还是自称“吾”、“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略有差异。但总体上看,这两种自称始终是同时并存的,问题只是哪个用得多一点,哪个用得少一点而已。一般而言,在比较正式、严肃的场合,皇帝自称为“朕”,而在比较轻松、随意的场合,则多自称“吾”或“我”。
像现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或影视剧那样,皇帝不分场合一律自称“朕”,“朕吃饭了”、“朕困了”、“朕喜欢你”、“朕不能没有你”、“朕射你无罪”,是不存在的。